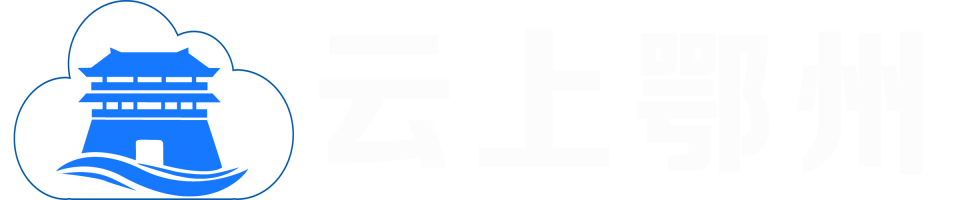дҪӣж•ҷиҮӘжұүд»Јдј е…ҘдёӯеӣҪпјҢж—©жңҹдё»иҰҒеңЁиҘҝе®үгҖҒжҙӣйҳіејҖе§ӢиҜ‘з»Ҹжҙ»еҠЁпјҢ并жңүйҷҗең°жөҒдј дәҺе®«е»·д№ӢдёӯгҖӮдёңжұүжң«е№ҙеҲ°дёүеӣҪж—©жңҹпјҢдҪӣж•ҷејҖе§Ӣз”ұе®«е»·иҝӣе…Ҙжҷ®йҖҡзҷҫ姓зҡ„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пјҢйҖҗжёҗеҜ№жҷ®йҖҡдёӯеӣҪдәәзҡ„з”ҹжҙ»дә§з”ҹе…·дҪ“еҪұе“ҚгҖӮеңЁиҝҷдёӘ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дҪңдёәдҪӣж•ҷд»Һе®«е»·дј е…ҘзӨҫдјҡгҖҒд»Һжҙӣйҳідј еҗ‘жұҹеҚ—жңҖж—©ж—¶жңҹзҡ„еҹәең°пјҢеҜ№дҪӣж•ҷеңЁж№–еҢ—д»ҘеҸҠж•ҙдёӘжұҹеҚ—ең°еҢәзҡ„дј ж’ӯдә§з”ҹдәҶйҮҚиҰҒеҪұе“ҚгҖӮ
еҺҶеҸІж–ҮзҢ®гҖҒдҪӣж•ҷе…ёзұҚе’ҢеҸӨд»ЈжӯҰжҳҢең°ж–№еҸІеҝ—еӨҡжңүж—©жңҹдҪӣж•ҷз»Ҹй„Ӯе·һеҗ‘жұҹеҚ—дј ж’ӯзҡ„е…·дҪ“и®°иҪҪгҖӮпјҲжўҒпјүйҮҠеғ§зҘҗж’°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гҖӢпјҲеҸҲеҗҚгҖҠеғ§зҘҗеҪ•гҖӢгҖҒгҖҠзҘҗеҪ•гҖӢпјүи®°иҪҪпјҢж”Ҝи°ҰвҖңзҢ®еёқд№Ӣжң«пјҢжұүе®ӨеӨ§д№ұпјҢдёҺд№Ўдәәж•°еҚҒе…ұеҘ”дәҺеҗҙгҖӮ---еҗҺеҗҙдё»еӯҷжқғй—»е…¶еҚҡеӯҰжңүжүҚж…§пјҢеҚіеҸ¬и§Ғд№ӢгҖӮвҖқпјҲе®ӢпјүйҮҠеҝ—зЈҗж’°гҖҠдҪӣзҘ–з»ҹи®°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й»„еҲқе…ғе№ҙпјҢеҗҙдё»еӯҷжқғдәҺжӯҰжҳҢе»әжҳҢд№җеҜәвҖқгҖӮиҝҷйҮҢзҡ„й»„еҲқе…ғе№ҙжҳҜжӣ№йӯҸзәӘе№ҙпјҢеҚіе…¬е…ғ220е№ҙпјҢиҝҷжҳҜи§ҒдәҺж–ҮзҢ®и®°иҪҪжұҹеҚ—жңҖж—©зҡ„дҪӣж•ҷеҜәйҷўгҖӮгҖҠдёӯеӣҪдҪӣж•ҷеҸІгҖӢпјҲ任继ж„Ҳдё»зј–пјүиӮҜе®ҡпјҡвҖңжұҹеҚ—иҜ‘з»ҸпјҢе§ӢдәҺжӯҰжҳҢпјҢзӣӣдәҺе»әдёҡвҖқгҖӮгҖҠж№–еҢ—ж–ҮеҢ–еҸІгҖӢпјҲе‘Ёз§ҜжҳҺдё»зј–пјүжӣҙе…·дҪ“еҲҶжһҗпјҡвҖңеӯҷжқғдёҚд»…ж”ҜжҢҒж”Ҝи°Ұзҡ„иҜ‘з»ҸпјҢиҖҢдё”еңЁжӯҰжҳҢе»әз«ӢжҳҢд№җеҜәпјҢжҪҳеӨ«дәәеҸҲеңЁжӯҰжҳҢе»әж…§е®қеҜәпјҢиҝҷдәӣеқҮдёәж№–еҢ—жңҖж—©зҡ„еҜәеәҷпјҢдёәдҪӣж•ҷеңЁж№–еҢ—зҡ„иҝӣдёҖжӯҘеҸ‘еұ•еҘ е®ҡдәҶеҹәзЎҖвҖқгҖӮ
дј—еӨҡж–ҮзҢ®и®°иҪҪиЎЁжҳҺпјҢдҪӣж•ҷеҲқдј 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пјҢжҳҜдҪӣж•ҷеңЁж№–еҢ—д»ҘеҸҠж•ҙдёӘжұҹеҚ—ең°еҢәдј ж’ӯзҡ„жәҗеӨҙд№ӢдёҖгҖӮ
1.жұүжң«ж”Ҝи°ҰеңЁ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иҜ‘з»Ҹ
ж”Ҝи°ҰжҳҜжұүжң«еҲ°дёүеӣҪж—¶жңҹи‘—еҗҚзҡ„дҪӣж•ҷиҜ‘з»ҸеӨ§еёҲпјҢеҜ№дҪӣж•ҷеңЁдёӯеӣҪзҡ„дј ж’ӯжңүйҮҚиҰҒеҪұе“ҚгҖӮжұүзҢ®еёқжң«жңҹпјҢж”Ҝи°ҰзҺҮдј—иҮӘжҙӣйҳіеҚ—жқҘеҗҙең°гҖӮпјҲжўҒпјүйҮҠж…§зҡҺж’°гҖҠй«ҳеғ§еҚ·В·йӯҸеҗҙе»әдёҡе»әеҲқеҜәеә·еғ§дјҡ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ж—¶еӯҷжқғе·ІеҲ¶жұҹе·ҰпјҢиҖҢдҪӣж•ҷжңӘиЎҢгҖӮе…Ҳжңүдјҳе©ҶеЎһж”Ҝи°ҰпјҢеӯ—жҒӯжҳҺпјҢдёҖеҗҚи¶ҠпјҢжң¬жңҲж”ҜдәәпјҢжқҘжёёжұүеўғгҖӮвҖқж”Ҝи°ҰдҪңдёәејҖйЈҺж°”д№Ӣе…ҲиҖ…жқҘеҲ°еҗҙең°пјҢеңЁй„ӮеҺҝпјҲеҗҺж”№еҗҚжӯҰжҳҢпјүиҜ‘з»Ҹж’ӯж•ҷпјҢ并еҫ—еӯҷжқғвҖңе® з§©вҖқдҪҝвҖңиҫ…еҜјдёңе®«вҖқпјҢеҺҶж—¶еҚҒеӨҡе№ҙгҖӮ
пјҲ1пјүж”Ҝи°Ұе…¶дәә
пјҲжўҒпјүйҮҠеғ§зҘҗ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ж”Ҝи°Ұдј гҖӢе…Ёж–Ү690еӯ—пјҢи®°иҪҪдәҶж”Ҝи°Ұз”ҹе№іеұҘеҺҶзҡ„дёҖдәӣеҹәжң¬жғ…еҶөпјҡ
ж”Ҝи°ҰжҳҜеӨ§жңҲж”ҜдәәпјҢд»–зҘ–зҲ¶ж”Ҝжі•еәҰеңЁжұүзҒөеёқж—¶пјҢзҺҮж•°зҷҫж—ҸдәәеҪ’еҢ–жұүжңқпјҢиў«е°ҒдёәзҺҮе–„дёӯйғҺе°ҶпјҲеҪ“ж—¶е®үзҪ®еӨ–ж—ҸйҰ–йўҶзҡ„й«ҳзә§жқӮиҒҢпјүгҖӮж”Ҝи°ҰиҮӘе№је°ұиЎЁзҺ°еҮәйқһеҗҢдёҖиҲ¬зҡ„ж…ҲжӮІд№ӢеҝғпјҢдёғеІҒж—¶пјҢд»–еңЁйӮ»еұ…家游жҲҸпјҢиў«зӢ—е’¬дјӨиғ«йӘЁпјҢйӮ»еұ…иҰҒжқҖзӢ—еү–иӮқдёәд»–жІ»дјӨеҸҚиў«д»–еҠқйҳ»гҖӮеҚҒеІҒејҖе§ӢиҜ»д№ҰпјҢиЎЁзҺ°еҮәйқһеҮЎзҡ„иҒӘж•ҸгҖӮеҚҒдёүеІҒиө·еӯҰиғЎиҜӯпјҢйҖҡжҷ“е…ӯеӣҪиҜӯиЁҖгҖӮж”Ҝи°Ұд»ҺеӯҰдәҺж”Ҝи°¶зҡ„ејҹеӯҗж”Ҝдә®пјҢеҚҡи§ҲзҫӨз»ҸпјҢеҸҲе№ҝжіӣеӯҰд№ еҗ„з§ҚзҹҘиҜҶпјҢ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зҹҘиҜҶжёҠеҚҡзҡ„еӯҰиҖ…гҖӮ
ж”Ҝи°Ұиә«жқҗзҳҰй«ҳпјҢзҡ®иӮӨй»қй»‘пјҢзңјзҷҪеӨҡпјҢзңјзҸ жҳҜй»„зҡ„гҖӮж—¶дәәйғҪиҜҙпјҡж”ҜйғҺж”ҜйғҺзңјдёӯй»„пјҢеҪўдҪ“иҷҪз»ҶжҳҜжҷәеӣҠгҖӮ
жұүзҢ®еёқжң«е№ҙпјҢж”Ҝи°ҰдёҺж•°еҚҒд№ЎдәәдёҖиө·йҒҝд№ұе…ҘеҗҙгҖӮж—¶еӯҷжқғе·ІжҺ§еҲ¶жұҹе·ҰпјҢеҗ¬иҜҙж”Ҝи°ҰиҒӘж…§еҚҡеӯҰпјҢдҫҝеҸ¬и§Ғж”Ҝи°ҰиҜўй—®дҪӣз»Ҹдёӯзҡ„ж·ұйҡҗд№Ӣд№үпјҢж”Ҝи°Ұеә”жңәйҮҠйҡҫпјҢж— жүҖдёҚи§ЈпјҢеӯҷжқғеӨ§дёәиөһиөҸпјҢжӢңж”Ҝи°ҰдёәеҚҡеЈ«пјҢд»Өд»–иҫ…еҜјеӨӘеӯҗпјҢз”ҡдёәйҮҚи§ҶгҖӮ
д№ӢеҗҺпјҢж”Ҝи°Ұй•ҝжңҹеңЁеҗҙең°зҝ»иҜ‘дҪӣз»ҸгҖӮе…¬е…ғ222е№ҙеҲ°253е№ҙпјҢиҜ‘еҮәгҖҠз»ҙж‘©иҜҳгҖӢгҖҠеӨ§иҲ¬жіҘжҙ№гҖӢгҖҠжі•еҸҘгҖӢгҖҠз‘һеә”жң¬иө·гҖӢзӯүдәҢеҚҒдёғйғЁз»Ҹе…ёпјҢиҜ‘иҫһж–Үйӣ…пјҢ并且еҸҚжҳ дәҶз»Ҹе…ёзҡ„жң¬д№ү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ж”Ҝи°Ұиҝҳж №жҚ®гҖҠж— йҮҸеҜҝз»ҸгҖӢгҖҒгҖҠдёӯжң¬иө·з»ҸгҖӢеҲӣдҪңдәҶгҖҠиөһиҸ©иҗЁиҝһеҸҘжўөе‘—гҖӢдёүеҘ‘пјҢжіЁгҖҠдәҶжң¬з”ҹжӯ»з»ҸгҖӢгҖӮеҗҙеӨӘеӯҗеҚідҪҚд»ҘеҗҺпјҢж”Ҝи°Ұйҡҗеұ…дәҺз©№йҡҳеұұпјҢдёҚдәӢдҝ—еҠЎпјҢи·ҹйҡҸз«әжі•е…°пјҢдҝ®жҢҒдә”жҲ’пјҢеҫҖжқҘеҸӘжңүеғ§дәәгҖӮеҗҺеҚ’дәҺеұұдёӯпјҢдә«е№ҙе…ӯеҚҒеІҒгҖӮеҪ“ж—¶зҡ„еҗҙеёқеӯҷдә®еңЁеҶҷз»ҷеғ§дәәзҡ„дҝЎдёӯиҜҙпјҡж”ҜжҒӯжҳҺдёҚеҢ»жІ»иҮӘе·ұзҡ„з–ҫз—…пјҢе…¶иЎҢдёәеҶІж·Ўжңҙзҙ пјҢе§Ӣз»ҲеҖјеҫ—жҷҜд»°пјҢжҲ‘дёәд№ӢжҒ»жҖҶпјҢдёҚиғҪиҮӘе·ІгҖӮ
ж—©жңҹд»Ӣз»Қж”Ҝи°Ұз”ҹе№ізҡ„дҪӣж•ҷе…ёзұҚпјҢдё»иҰҒжңүеҚ—еҢ—жңқж—¶жңҹпјҲжўҒпјүйҮҠеғ§зҘҗж’°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гҖӢпјҢе…¶дёӯж¶үеҸҠж”Ҝи°Ұз”ҹе№ізҡ„жңүеҚ·дёғ收еҪ•зҡ„ж”Ҝж•ҸеәҰжүҖж’°гҖҠеҗҲйҰ–жҘһдёҘз»Ҹи®°гҖӢе’ҢеҚ·еҚҒдёүгҖҠж”Ҝи°Ұдј гҖӢгҖӮзЁҚжҷҡзҡ„пјҲжўҒпјүйҮҠж…§зҡҺж’°гҖҠй«ҳеғ§дј гҖӢпјҢз”ұдәҺж”Ҝи°ҰжҳҜеңЁе®¶еұ…еЈ«пјҢжІЎжңүеҚ•зӢ¬еҲ—дј пјҢиҖҢжҳҜе°Ҷд»Ӣз»Қж”Ҝи°Ұз”ҹе№ізҡ„еҶ…е®№йҷ„еҪ•дәҺеҚ·дёҖгҖҠйӯҸеҗҙе»әдёҡе»әеҲқеҜәеә·еғ§дјҡгҖӢд№ӢдёӯпјҢдё”д»Ӣз»Қзҡ„еҶ…е®№жҜ”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ж”Ҝи°Ұдј гҖӢзӣёеҜ№зІ—з•ҘгҖӮз”ұдәҺдёҠиҝ°дёүеӨ„йғҪжІЎжңүе…ідәҺж”Ҝи°Ұз”ҹжҙ»е№ҙд»ЈгҖҒеҚ—жқҘеҲ°й„ӮеҺҝд»ҘеҸҠдёңеҺ»е»әдёҡе…·дҪ“ж—¶й—ҙзҡ„и®°иҪҪпјҢеӣ жӯӨеҗ„з§ҚдҪӣж•ҷеҸІж–ҮзҢ®еҜ№ж”Ҝи°Ұз”ҹе№іеұҘеҺҶзҡ„и®°иҝ°еӨҡжҜ”иҫғжЁЎзіҠпјҢз”ҡиҮіеӯҳеңЁдёҚе°‘иҜҜи§Је’Ңи®№дј гҖӮ
пјҲ2пјүжұүжң«еҘ”еҗҙе…Ҙй„Ӯ
жңүе…іж”Ҝи°Ұз”ҹжҙ»зҡ„е№ҙд»ЈпјҢвҖңеҚ—дә¬еҺҶеҸІж–ҮеҢ–еҗҚдәәзі»еҲ—дёӣд№ҰвҖқгҖҠж”Ҝи°Ұдј гҖӢпјҲзҺӢжҜ“и‘—пјүпјҢжўізҗҶдәҶдҪӣж•ҷе…ёзұҚдёӯзҡ„еҗ„з§Қйӣ¶ж•ЈдҝЎжҒҜпјҢз»јеҗҲеҲӨж–ӯж”Ҝи°ҰеӨ§зәҰз”ҹжҙ»еңЁе…¬е…ғ195е№ҙ--255е№ҙгҖӮе…¶дҫқжҚ®дё»иҰҒжҳҜж №жҚ®еӯҷдә®жӮјдәЎд№Ұзҡ„ж—¶й—ҙд»ҘеҸҠж”Ҝи°Ұдё–еҜҝе…ӯеҚҒжҺЁз®—иҖҢжқҘгҖӮж”Ҝи°ҰиҷҪдёәеӨ–еҹҹдәәпјҢдҪҶз”ҹдәҺжұүең°пјҢж•…ж”Ҝж•ҸеәҰжңүиЁҖвҖңи¶ҠеңЁжұүз”ҹвҖқгҖӮж”Ҝи°ҰеҚ—иҝҒеҗҙең°д№ӢеүҚпјҢеңЁжҙӣйҳіеҸ—еӯҰдәҺж”Ҝдә®гҖӮеҚ—иҝҒеҘ”еҗҙд»ҘеҗҺпјҢе…Ҳй©»жӯҰжҳҢпјҲеҪ“ж—¶дёәй„ӮеҺҝпјҢзЁҚеҗҺж”№дёәжӯҰжҳҢпјүпјҢеҗҺеҺ»е»әдёҡгҖӮ
ж”Ҝи°ҰеҘ”еҗҙе…Ҙй„Ӯзҡ„е…·дҪ“ж—¶й—ҙпјҢзҺ°еңЁйңҖиҰҒд»Һж—©жңҹдҪӣж•ҷе…ёзұҚйҮҢиҜёеӨҡйӣ¶ж•Ји®°иҪҪзҡ„еҲҶжһҗдёӯеҫ—еҮәз»“и®әгҖӮ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ж”Ҝи°Ұдј гҖӢи®°иҪҪвҖңзҢ®еёқд№Ӣжң«пјҢжұүе®ӨеӨ§д№ұпјҢдёҺд№Ўдәәж•°еҚҒе…ұеҘ”дәҺеҗҙвҖқгҖӮгҖҠй«ҳеғ§еҚ·В·йӯҸеҗҙе»әдёҡе»әеҲқеҜәеә·еғ§дјҡгҖӢд№ҹжңүж”Ҝи°ҰвҖңжұүзҢ®жң«д№ұпјҢйҒҝең°дәҺеҗҙвҖқзҡ„и®°иҪҪгҖӮжӣ№дё•еәҹжұүзҢ®еёқиҮӘз«ӢеңЁе…¬е…ғ220е№ҙ10жңҲпјҢдёңжұүз»“жқҹпјҢеҺҶеҸІиҝӣе…ҘдёүеӣҪж—¶д»ЈгҖӮж”Ҝи°ҰвҖңжұүзҢ®жң«д№ұвҖқеҘ”еҗҙпјҢе…·дҪ“ж—¶й—ҙеә”иҜҘеңЁе…¬е…ғ220е№ҙжҲ–иҖ…зЁҚж—©д№ӢеүҚгҖӮеҸҲжҚ®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ж”Ҝи°Ұдј гҖӢвҖңж”Ҝи°Ұй•ҝжңҹеңЁеҗҙең°зҝ»иҜ‘дҪӣз»ҸгҖӮй»„жӯҰе…ғе№ҙиҮіе»әе…ҙдёӯпјҲеҚіе…¬е…ғ222е№ҙеҲ°253е№ҙпјүпјҢиҜ‘еҮәгҖҠз»ҙж‘©иҜҳгҖӢзӯүдәҢеҚҒдёғйғЁз»Ҹе…ёвҖқзҡ„и®°иҪҪпјҢиҜҙжҳҺе…¶д»Һй»„жӯҰе…ғе№ҙпјҲеҚіе…¬е…ғ222е№ҙпјүе°ұе·Із»ҸејҖе§ӢдәҶеңЁеҗҙең°зҡ„иҜ‘з»Ҹжҙ»еҠЁгҖӮеҶҚжҚ®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е®үзҺ„дј гҖӢдёӯе…ідәҺз»ҙзҘҮйҡҫзҡ„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еҗҺжңүжІҷй—Ёз»ҙзҘҮйҡҫиҖ…пјҢеӨ©з«әдәәд№ҹгҖӮд»Ҙеӯҷжқғй»„жӯҰдёүе№ҙиөҚгҖҠжҳҷй’өз»ҸгҖӢиғЎжң¬жқҘиҮіжӯҰжҳҢгҖӮгҖҠжҳҷй’өгҖӢеҚі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д№ҹгҖӮж—¶ж”Ҝи°ҰиҜ·еҮәз»ҸпјҢд№ғд»Өе…¶еҗҢйҒ“з«әе°ҶзӮҺдј иҜ‘пјҢи°ҰеҶҷдёәжұүж–ҮвҖқпјҢеҸҜд»ҘиӮҜе®ҡпјҢж”Ҝи°ҰиҮӘжҙӣйҳіеҚ—жқҘеҗҙең°пјҢжүҖеҲ°д№ӢеӨ„е°ұжҳҜжұҹеҚ—й„ӮеҺҝпјҢеҚізЁҚеҗҺдёңеҗҙе»әйғҪзҡ„жӯҰжҳҢгҖӮиҖҢдё”ж”Ҝи°ҰжқҘеҲ°жӯҰжҳҢдёҚд№…пјҢеҚ°еәҰеғ§дәәз»ҙзҘҮйҡҫе’Ңз«әеҫӢзӮҺдәҺй»„жӯҰдёүе№ҙеҚіе…¬е…ғ224е№ҙвҖңжқҘйҖӮжӯҰжҳҢвҖқпјҢз»ҙзҘҮйҡҫеёҰжқҘжўөж–Үжң¬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пјҲеҚігҖҠжҳҷй’өз»ҸгҖӢпјүпјҢз”ұз«әеҫӢзӮҺеҸЈиҜ‘пјҢж”Ҝи°Ұ笔еҪ•пјҢдёүдәәеңЁжӯҰжҳҢеҗҲдҪңиҜ‘еҮәдәҶдёӯеӣҪдҪӣж•ҷеҸІдёӯжһҒ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дәҢеҚ·гҖӮиҮідәҺпјҲе®ӢпјүйҮҠеҝ—зЈҗж’°гҖҠдҪӣзҘ–з»ҹи®°гҖӢи®°иҪҪвҖңй»„еҲқдә”е№ҙпјҲ224е№ҙпјүпјҢжңҲж”ҜеӣҪдјҳе©ҶеЎһж”Ҝи°ҰжқҘжҙӣйҳіпјҢ---еҗҺйҒҝең°еҪ’еҗҙвҖқпјҢжҷ®йҒҚи®Өдёәе…¶дёӯжүҖи®°иҪҪзҡ„ж—¶й—ҙжңүиҜҜгҖӮ
ж”Ҝи°Ұжұүжң«еҘ”еҗҙе…Ҙй„ӮпјҢе®Ңе…Ёз¬ҰеҗҲеҪ“ж—¶зҡ„еҺҶеҸІиғҢжҷҜгҖӮдёңжұүжң«е№ҙпјҢдёӯеҺҹжҲҳд№ұдёҚжӯўпјҢеӨ§жү№еҢ—ж–№дәәеЈ«дёәйҒҝжҲҳзҘёиҖҢзә·зә·йҖғзҰ»еҚ—иҝҒпјҢе…¶дёӯд№ҹжңүйғЁеҲҶдҪӣж•ҷдҝЎеҫ’гҖӮжҚ®гҖҠдёүеӣҪеҝ—гҖӢи®°иҝ°пјҢе…¬е…ғ208е№ҙзҡ„иөӨеЈҒд№ӢжҲҳпјҢеҘ е®ҡдәҶеӨ©дёӢдёүеҲҶзҡ„еҹәжң¬ж јеұҖгҖӮжҲҳеҗҺдҪңдёәеӯҷеҲҳиҒ”еҶӣеӨ§жң¬иҗҘзҡ„жұҹеҚ—й„ӮеҺҝпјҢжқҘиҮӘеҢ—ж–№зҡ„еЁҒиғҒеҹәжң¬и§ЈйҷӨгҖӮдҪҶжҳҜжҺҘдёӢжқҘпјҢеӯҷеҲҳдёәдәүиҚҶе·һзҹӣзӣҫеҶҚиө·гҖӮе…¬е…ғ220е№ҙпјҢеҗҙеӣҪеңЁеӨҚеҫ—иҚҶе·һеҗҺдёҺе…ҙе…өиҖҢиҮізҡ„иңҖеҶӣеҶіжҲҳеӨ·йҷөпјҢдәҺжҳҜе№ҙй—°е…ӯжңҲеҸ–еҫ—еҶіе®ҡжҖ§зҡ„еӨ·йҷөеӨ§жҚ·пјҢиҘҝеҗ‘е®үе…ЁйҡҗжӮЈд№ҹе®Ңе…Ёи§ЈйҷӨпјҢеӯҷеҗҙе®Ңе…ЁжҺ§еҲ¶дәҶй•ҝжұҹдёӯжёёеҚ—еІёгҖӮдәҺжӯӨжғ…еҠҝд№ӢдёӢпјҢж”Ҝи°ҰеҚ—иҝҒжқҘеҲ°еҗҙең°й„ӮеҺҝпјҢеҫҲеҝ«еҸ—еҲ°еӯҷжқғзҡ„йҮҚи§ҶгҖӮе…¬е…ғ221е№ҙ4жңҲпјҢеӯҷжқғиҮӘе…¬е®ү(д»Ҡж№–еҢ—е…¬е®ү)иҝҒйғҪй„ӮеҺҝ(д»Ҡж№–еҢ—й„Ӯе·һ)пјҢе°Ҷй„ӮеҺҝж”№еҗҚдёәжӯҰжҳҢгҖӮжӯҰжҳҢдҪңдёәеҗҙеӣҪзҡ„еӨ§жң¬иҗҘпјҢиҝӣиҖҢеҗёеј•жӣҙеӨҡдҪӣж•ҷеғ§дј—иҒҡйӣҶпјҢз»ҙзҘҮйҡҫе’Ңз«әеҫӢзӮҺе°ұжҳҜжңҖж—©ж…•еҗҚжқҘеҲ°жӯҰжҳҢ并дёҺж”Ҝи°ҰеҗҲдҪңиҜ‘з»Ҹзҡ„еӨ–еҹҹй«ҳеғ§гҖӮ
д»Һж—¶й—ҙзәҝдёҠжўізҗҶпјҢж”Ҝи°ҰзӯүдәәеҘ”еҗҙе…Ҙй„ӮпјҢеңЁ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иҜ‘з»Ҹж’ӯж•ҷпјҢжҳҜдҪӣж•ҷеңЁжұҹеҚ—ең°еҢәжҙ»еҠЁзҡ„ејҖз«ҜгҖӮеҜ№дҪӣж•ҷеңЁжұҹеҚ—ең°еҢәзҡ„е№ҝжіӣдј ж’ӯпјҢе…·жңүйҮҚеӨ§иҖҢдё”ж·ұиҝң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
пјҲ3пјүз»ҙзҘҮйҡҫвҖңжқҘйҖӮжӯҰжҳҢвҖқ
ж”Ҝи°ҰжҳҜжңҖж—©еҲ°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иҜ‘з»Ҹж’ӯж•ҷзҡ„дҪӣж•ҷеұ…еЈ«пјҢз»ҙзҘҮйҡҫеҲҷжҳҜжңҖж—©жқҘ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иҜ‘з»Ҹдј ж•ҷзҡ„еҚ°еәҰеғ§дәәгҖӮ
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жі•еҸҘз»ҸеәҸгҖӢжҸҗеҲ°пјҡвҖңе§ӢиҖ…з»ҙзҘҮйҡҫеҮәиҮӘеӨ©з«әгҖӮд»Ҙй»„жӯҰдёүе№ҙжқҘйҖӮжӯҰжҳҢгҖӮд»Ҷд»ҺеҸ—жӯӨдә”зҷҫеҒҲжң¬пјҢиҜ·е…¶еҗҢйҒ“з«әе°ҶзӮҺдёәиҜ‘гҖӮвҖқ
жҚ®гҖҠй«ҳеғ§еҚ·В·йӯҸеҗҙжӯҰжҳҢз»ҙзҘҮйҡҫгҖӢи®°иҪҪпјҢз»ҙзҘҮйҡҫдёәеҚ°еәҰдәәпјҢ其家ж—ҸдҝЎеҘүжӢңзҒ«ж•ҷпјҢд»–дәҰд»ҘзҒ«зҘҖдёәжңҖдёҠд№Ӣжі•гҖӮеҗҺеҸ—дёҖжІҷй—ЁеҪұе“ҚпјҢд№ғиҲҚејғж—§ж—ҘжүҖеӯҰиҖҢеҪ’дҫқдҪӣж•ҷгҖӮжңүж•…дәӢиҝ°е…¶зјҳз”ұз§°пјҢеҪ“ж—¶жңүдёҖд№ еӯҰе°Ҹд№ҳгҖҒе–„иЎҢйҒ“жңҜзҡ„жІҷй—ЁдәҺж—Ҙжҡ®ж—¶еҲҶжқҘеҲ°д»–家门еүҚпјҢеёҢжңӣжҠ•е®ҝгҖӮз”ұдәҺдҝЎд»°дёҚеҗҢпјҢеӨҡжңүзҢңеҝҢпјҢз»ҙ家й—ӯй—ЁдёҚзәіпјҢжІҷй—ЁеҸӘеҘҪйңІе®ҝй—ЁеӨ–гҖӮжҳҜеӨңпјҢжІҷй—Ёжҡ—ж–Ҫе’’жі•пјҢдҪҝеҫ—з»ҙзҘҮйҡҫ家жүҖдәӢд№ӢзҒ«ж¬»з„¶еҸҳзҒӯгҖӮз»ҙ家еӨ§жғҠпјҢдәҺжҳҜдёҫ家иҖҢеҮәпјҢжӢңиҜ·жІҷй—Ёе…Ҙе®Өдҫӣе…»гҖӮжІҷй—ЁеӨҚд»Ҙе’’жңҜдҪҝзҒ«йҮҚзҮғгҖӮз»ҙзҘҮйҡҫи§ҒжІҷй—ЁзҘһеҠӣиҝңиғңдәҺе·ұпјҢйҒӮдәҺдҪӣжі•еӨ§з”ҹдҝЎеҝғпјҢеқҡеҶіж”ҫејғжҳ”ж—ҘжүҖеӯҰпјҢеҮә家дёәйҒ“пјҢеҗҺж·ұ究дёүи—ҸпјҢ并зү№зІҫдәҺеӣӣйҳҝеҗ«з»ҸгҖӮжёёеҢ–иҜёеӣҪпјҢиҺ«дёҚеҘүе…¶дёәеёҲгҖӮдёүеӣҪеҗҙй»„жӯҰдёүе№ҙпјҲ224е№ҙпјүпјҢдёҺз«әеҫӢзӮҺжҗәжўөжң¬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еҗҢжқҘжӯҰжҳҢгҖӮеҪ“ж—¶еҗҙең°дәәеЈ«иҜ·д»–们еҮәз»ҸпјҢ然еҗҺе…ұеҗҢе°ҶиҜҘз»ҸиҜ‘еҮәпјҢеҫ—2еҚ·гҖӮеҗҺеҸҲиҜ‘гҖҠйҳҝе·®жң«иҸ©иҗЁз»ҸгҖӢ4еҚ·гҖӮз”ұдәҺдәҢеғ§дёҚе–„жұүж–ҮпјҢж•…иҜ‘з»Ҹж–ҮиҫһйўҮжңүжңӘиғҪе°Ҫд№үд№ӢеӨ„гҖӮеҗҺдәәиҜ„е…¶иҜ‘жң¬вҖңеҝ—еӯҳд№үжң¬пјҢиҫһиҝ‘жңҙиҙЁвҖқгҖӮ
дёҺз»ҙзҘҮйҡҫз»“дјҙжқҘеҲ°жӯҰжҳҢзҡ„з«әеҫӢзӮҺпјҢд№ҹеҗҚз«әе°ҶзӮҺпјҢгҖҠй«ҳеғ§еҚ·гҖӢйҮҢжІЎжңүе…¶еҚ•зӢ¬дј и®°гҖӮжўізҗҶдҪӣж•ҷе…ёзұҚзҡ„еҗ„з§Қйӣ¶ж•ЈдҝЎжҒҜеҸҜзҹҘпјҢз«әеҫӢзӮҺд№ҹдёәеҚ°еәҰеғ§дәәпјҢжүҖеӯҰеҚҡйҖҡеҶ…еӨ–пјҢзҹҘи§ЈдёҺдҝ®иЎҢйғҪеҫҲжё…еҮҖдёҘи°ЁгҖӮе…¬е…ғ224е№ҙдёҺз»ҙзҘҮйҡҫжҗәжўөжң¬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еҗҢжқҘжӯҰжҳҢпјҢвҖңе°ҶзӮҺиҷҪе–„еӨ©з«әиҜӯпјҢжңӘеӨҮжҷ“жұүвҖқпјҢдәҢдәәдёҺж”Ҝи°ҰеҗҲдҪңе°ҶиҜҘз»ҸиҜ‘еҮәпјҢеҫ—2еҚ·гҖӮз»ҙзҘҮйҡҫеҺ»дё–еҗҺпјҢз«әеҫӢзӮҺиҝҳдәҺй»„йҫҷдәҢе№ҙпјҲ230е№ҙпјүдёҺж”Ҝи°ҰеҗҲиҜ‘гҖҠж‘©зҷ»дјҪз»ҸгҖӢ2еҚ·гҖҒгҖҠдҪӣеҢ»з»ҸгҖӢ1еҚ·пјҢ并иҮӘиҜ‘гҖҠдёүж‘©з«ӯз»ҸгҖӢгҖҒгҖҠжўөеҝ—з»ҸгҖӢеҗ„1еҚ·гҖӮ
пјҲ4пјү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жҳҢд№җеҜә
пјҲе®ӢпјүйҮҠеҝ—зЈҗж’°гҖҠдҪӣзҘ–з»ҹи®°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й»„еҲқе…ғе№ҙпјҲ220е№ҙпјүпјҢеҗҙдё»еӯҷжқғдәҺжӯҰжҳҢе»әжҳҢд№җеҜәвҖқпјҢвҖңеӨӘе’Ңдёүе№ҙпјҲ229е№ҙпјүпјҢеҗҙжҪҳеӨ«дәәдәҺжӯҰжҳҢе»әж…§е®қеҜәвҖқгҖӮиҝҷжҳҜзҺ°еӯҳжңҖж—©е…ідәҺ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жҳҢд№җеҜәгҖҒж…§е®қеҜәзҡ„и®°иҪҪгҖӮжҚ®жӯӨи®°иҪҪпјҢжҳҢд№җеҜәгҖҒж…§е®қеҜәж— з–‘жҳҜж•ҙдёӘж№–еҢ—д№ғиҮіжұҹеҚ—ең°еҢәжңҖж—©зҡ„дҪӣж•ҷеҜәйҷўгҖӮ
еҗҙдё»еӯҷжқғй»„еҲқе…ғе№ҙдәҺжӯҰжҳҢе»әжҳҢд№җеҜәпјҢдёҺ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ж”Ҝи°Ұдј гҖӢдёӯжңүе…іж”Ҝи°ҰжұүзҢ®жң«д№ұеҘ”еҗҙзҡ„ж—¶й—ҙи®°иҪҪзӣёдә’з»ҹдёҖпјҢд№ҹдёҺж”Ҝи°ҰеҘ”еҗҙе…Ҳе…Ҙй„ӮпјҲжӯҰжҳҢпјүеҗҺеҺ»е»әдёҡзҡ„дәӢе®һеҲӨж–ӯзӣёдә’еҚ°иҜҒгҖӮвҖңеҗҙдё»еӯҷжқғй—»е…¶еҚҡеӯҰжңүжүҚж…§пјҢеҚіеҸ¬и§Ғд№ӢгҖӮеӣ й—®з»Ҹдёӯж·ұйҡҗд№Ӣд№үпјҢеә”жңәйҮҠйҡҫпјҢж— з–‘дёҚжһҗгҖӮжқғеӨ§жӮҰпјҢжӢңдёәеҚҡеЈ«гҖӮвҖқиҝҷдёӘиҝҮзЁӢдёӯвҖңеҗҙдё»еӯҷжқғдәҺжӯҰжҳҢе»әжҳҢд№җеҜәвҖқд»Ҙдёәж”Ҝи°ҰзӯүдәәиҜ‘з»Ҹж’ӯж•ҷд№ӢжүҖпјҢе®Ңе…ЁжҳҜйЎәзҗҶжҲҗз« д№ӢдәӢгҖӮиҖҢеұ…еЈ«иә«д»Ҫзҡ„ж”Ҝи°ҰзӯүиҒҡеұ…дҝ®иЎҢеңәжүҖпјҢе°‘и§ҒдәҺе”җе®Ӣд№ӢеүҚзҡ„ж—©жңҹдҪӣж•ҷе…ёзұҚпјҢд№ҹе®Ңе…Ёз¬ҰеҗҲж—©жңҹдҪӣж•ҷе…ёзұҚеҶ…е®№йҖүжӢ©зҡ„еҹәжң¬зү№еҫҒгҖӮдҪӣж•ҷзҡ„вҖңеҜәвҖқдәҰз§°вҖңдҪӣеҜәвҖқгҖҒвҖңеҜәйҷўвҖқпјҢжҳҜдҪӣж•ҷеғ§дј—дҫӣдҪӣе’ҢиҒҡеұ…дҝ®иЎҢзҡ„еңәжүҖпјҢжҳҜж•…вҖңжҳҢд№җеҜәвҖқд№ҹз§°вҖңжҳҢд№җйҷўвҖқгҖӮгҖҠж№–еҢ—ж–ҮеҢ–еҸІгҖӢиҖғиҜҒпјҡвҖңжҳҢд№җйҷўдёәж№–еҢ—еҜәйҷўд№Ӣе§ӢпјҢиҜҘйҷўе»әжҲҗеҗҺпјҢжұҹеҚ—иҜ‘з»Ҹе§Ӣз”ұе®ҳзҪІиҪ¬е…ҘеҜәйҷўвҖқгҖӮ
еҸӨд»ЈжӯҰжҳҢең°ж–№еҸІеҝ—зҡ„е…ідәҺжҳҢд№җеҜәзҡ„и®°иҪҪпјҢдёҺдёҠиҝ°дҪӣж•ҷе…ёзұҚзҡ„и®°иҪҪе®Ңе…ЁдёҖиҮҙгҖӮжё…е…үз»Ә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жҳҢд№җйҷўпјҢеңЁеҺҝеҚ—е…ӯйҮҢпјҢжұүе»әе®үдәҢеҚҒдә”е№ҙеӯҷжқғдҪңеҜәпјҢжңүдәҢжө®еӣҫпјҢдёңжңүжҲҙжёҠи®°пјҢиҘҝдёәи°ўе°ҡз«ӢзҹігҖӮе®ӢеҲқеәҹпјҢе…¶ең°дёәжӯҰжҳҢй•ҮгҖӮд»Ҡй•ҮдәҰеәҹгҖӮвҖқжұүе»әе®үдәҢеҚҒдә”е№ҙеҚіе…¬е…ғ220е№ҙпјҢдёҺгҖҠдҪӣзҘ–з»ҹи®°гҖӢзҡ„ж—¶й—ҙи®°иҪҪе®Ңе…ЁдёҖиҮҙгҖӮжё…е…үз»Ә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еҜ№жҳҢд№җеҜәзҡ„и®°иҪҪжәҗиҮӘд№ҫйҡҶгҖҒеә·зҶҷ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пјҢеә·зҶҷ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жәҗдәҺжҳҺд»Ј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пјҢиҖҢжҳҺд»Ј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еҲҷжәҗиҮӘеҚ—е®Ӣзҡ„гҖҠжӯҰжҳҢеңҹдҝ—зј–гҖӢгҖҒжҷӢд»Јзҡ„гҖҠжӯҰжҳҢи®°гҖӢпјҢе…¶дҝЎжҒҜжәҗеӨҙеңЁж—¶й—ҙдёҠе·Із»ҸеҚҒеҲҶжҺҘиҝ‘жұүжң«дёүеӣҪж—¶жңҹгҖӮе°Ҫз®ЎжҳҺд»ЈеҸҠд»ҘеүҚзҡ„жӯҰжҳҢең°ж–№еҸІеҝ—зҡҶе·Іж•ЈдҪҡпјҢдҪҶе…¶дёӯе…ідәҺжҳҢд№җеҜәзҡ„ең°зӮ№гҖҒжҙ»еҠЁгҖҒе…іиҒ”дәәзү©гҖҒеӯҳеәҹж—¶й—ҙжҜ”гҖҠдҪӣзҘ–з»ҹи®°гҖӢзҡ„и®°иҪҪжӣҙеҠ иҜҰз»ҶпјҢдё”дә’зӣёд№Ӣй—ҙйғҪиғҪеҚ°иҜҒеҗ»еҗҲпјҢеҸҜдҝЎеәҰжҳҜеҫҲй«ҳзҡ„гҖӮ
еҺҝеҝ—и®°иҪҪжҳҢд№җйҷўзҡ„ең°зӮ№вҖңеҺҝеҚ—е…ӯйҮҢвҖқпјҢеҚіеҺҹжӯҰжҳҢеҺҝеҺҝжІ»жүҖеңЁең°д»ҘеҚ—6йҮҢпјҢеұһжЁҠеұұд№ӢеҚ—зј“еқЎж»Ёж№–ең°еҢәгҖӮвҖңе®ӢеҲқеәҹпјҢе…¶ең°дёәжӯҰжҳҢй•ҮвҖқпјҢиҝҷдёӘең°ж–№е°ұжҳҜе®Ӣд»ЈжӯҰжҳҢеҶӣеңЁжӯҰжҳҢеҺҝзҡ„й©»ең°жӯҰжҳҢй•ҮгҖӮжңүй„Ӯе·һең°ж–№еҺҶеҸІж–ҮеҢ–з ”з©¶дәәеЈ«иҖғиҜҒпјҢе…¶е…·дҪ“ең°зӮ№еңЁд»ҠеӨ©зҡ„еҹҺеҢәдә”йҮҢеў©йҷ„иҝ‘гҖӮ
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еңЁдёӨжҷӢж—¶зҡ„ең°дҪҚд»Қ然еҚҒеҲҶжҳҫиҰҒгҖӮеҺҶеҸІи®°иҪҪпјҢзҺӢж•ҰгҖҒйҷ¶дҫғгҖҒеәҫдә®йғҪжӣҫз»Ҹд»ҘжұҹиҚҶиұ«еҲәеҸІиә«д»Ҫй•ҮжӯҰжҳҢпјҢи§ҶжӯҰжҳҢдёәеҶӣдәӢжҲҳз•ҘиҰҒең°гҖӮеҺҝеҝ—йҮҢи®°иҪҪзҡ„жҲҙжёҠпјҢдёәдёңжҷӢеҫҒиҘҝе°ҶеҶӣпјҢжӣҫз»ҸеҜ“еұ…жӯҰжҳҢпјҢеҗҺиў«зҺӢж•ҰжүҖе®іпјҢжӯ»еҗҺеңЁжӯҰжҳҢе®ү葬гҖӮи°ўе°ҡпјҢеҲҷжӣҫз»Ҹд»Ҙжұҹе·һеҲәеҸІиә«д»Ҫй•Үе®ҲжӯҰжҳҢгҖӮиҝҷдёӨдәәйғҪжҳҜдёңжҷӢжҳҫе®ҰпјҢеҲҶеҲ«дёәжҳҢд№җйҷўдҪңи®°йўҳзў‘пјҢдёҚд»…иҜҙжҳҺжҳҢд№җйҷўеңЁдёңжҷӢж—¶д»Қ然еӯҳеңЁпјҢиҖҢдё”еҪұе“ҚиҝҳйқһеҗҢдёҖиҲ¬гҖӮ
дёүеӣҪеҲқжңҹпјҢжӯҰжҳҢйҷӨжҳҢд№җйҷўеӨ–пјҢиҝҳе»әжңүдёӨеә§дҪӣеҜәпјҢж…§е®қеҜәдёҺе®қе®ҒйҷўгҖӮе…үз»Ә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иҪҪпјҡвҖңжғ пјҲж…§пјүе®қеҜәеңЁеҺҝдёңпјҢдё–дј еӯҷдә®жҪҳеӨ«дәәе»әпјҢжўҒеӨ§еҗҢй—ҙпјҢйӮөйҷөзҺӢиҗ§зә¶ж’°зў‘пјҢд№…еәҹгҖӮвҖқвҖңе®қе®ҒйҷўеңЁеҺҝдёңдёҖзҷҫе…«еҚҒжӯҘпјҢдё–дј еӯҷеҗҙе»әйғҪж—¶з«ӢвҖқгҖӮеҺҝеҝ—и®°иҪҪзҡ„иҝҷдёӨеә§дҪӣеҜәең°зӮ№пјҢйғҪеңЁеҪ“ж—¶зҡ„иҘҝеұұдёңйә“пјҢеҗҙзҺӢеҹҺиҫ№гҖӮиҝҷдёҚд»…иҜҙжҳҺеҪ“ж—¶жӯҰжҳҢзҡ„иҜ‘з»Ҹдј ж•ҷжҙ»еҠЁеңЁж”Ҝи°ҰгҖҒз»ҙзҘҮйҡҫд»ҘеӨ–иҝҳеӨ§жңүдәәеңЁпјҢиҖҢдё”иҝҷдәӣиҜ‘з»Ҹдј ж•ҷжҙ»еҠЁдёҺеҗҙеӣҪзҡ„е®«е»·дҝқжҢҒзқҖеҫҲиҝ‘зҡ„и·қзҰ»пјҢеӯҳеңЁзқҖеҫҲеҜҶеҲҮзҡ„иҒ”зі»гҖӮ
пјҲ5пјүиҫ…еҜјдёңе®«еҸҠдёңиҝҒе»әдёҡ
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ж”Ҝи°Ұдј гҖӢе…ідәҺеӯҷжқғеҜ№ж”Ҝи°ҰвҖңдҪҝиҫ…еҜјдёңе®«вҖқзҡ„и®°иҪҪпјҢеҸҜи°“зқҖеўЁдёҚе°‘пјҢеҚҒеҲҶиӮҜе®ҡпјҡвҖңеҗҙдё»еӯҷжқғй—»е…¶еҚҡеӯҰжңүжүҚж…§пјҢеҚіеҸ¬и§Ғд№ӢгҖӮеӣ й—®з»Ҹдёӯж·ұйҡҗд№Ӣд№үпјҢеә”жңәйҮҠйҡҫпјҢж— з–‘дёҚжһҗгҖӮжқғеӨ§жӮҰпјҢжӢңдёәеҚҡеЈ«пјҢдҪҝиҫ…еҜјдёңе®«пјҢз”ҡеҠ е® з§©гҖӮвҖқдҪҶжҳҜпјҢе…¶дёӯжІЎжңүи®°иҪҪеӯҷжқғеҸ¬и§Ғж”Ҝи°Ұзҡ„е…·дҪ“ж—¶й—ҙ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жҳҺзЎ®и®°еҪ•ж”Ҝи°ҰдҪ•ж—¶иҺ·еҫ—еӨӘеӯҗеӨӘеӮ…зҡ„еӨҙиЎ”пјҢеӣ жӯӨвҖңдҪҝиҫ…еҜјдёңе®«вҖқзҡ„еҜ№иұЎжӣҫз»ҸеӯҳеңЁдёҚеҗҢзҡ„и®ӨиҜҶпјҢеҪ“д»Ји‘—еҗҚдҪӣеӯҰ家жұӨз”ЁеҪӨгҖҒеҗ•жҫӮзӯүиӮҜе®ҡжҳҜеҗҙеӣҪ第дёҖд»»еӨӘеӯҗеӯҷзҷ»гҖӮеҚ—дә¬еӨ§еӯҰе“ІеӯҰпјҲе®—ж•ҷеӯҰпјүзі»ж•ҷжҺҲжқЁз»ҙдёӯеҲҷж №жҚ®гҖҠй«ҳеғ§дј гҖӢгҖҒгҖҠдёүеӣҪеҝ—гҖӢжңүе…іи®°иҪҪпјҢеҲҶжһҗдёәе…¬е…ғ242е№ҙиў«з«ӢдёәеӨӘеӯҗгҖҒе…¬е…ғ250е№ҙиў«еәҹй»ңзҡ„еӯҷе’ҢгҖӮдёҚиҝҮпјҢж №жҚ®еҺҶеҸІж–ҮзҢ®гҖҒдҪӣж•ҷе…ёзұҚе’ҢеҸӨд»ЈжӯҰжҳҢең°ж–№еҸІеҝ—жңүе…іи®°иҪҪз»јеҗҲеҲӨж–ӯпјҢж”Ҝи°ҰвҖңдҪҝиҫ…еҜјдёңе®«вҖқзҡ„еҜ№иұЎпјҢжҳҜе…¬е…ғ221е№ҙиў«з«ӢдёәзҺӢеӨӘеӯҗгҖҒ229е№ҙиў«з«ӢдёәзҡҮеӨӘеӯҗзҡ„еӯҷзҷ»йҖҗжёҗжҲҗдёәе®ҡи®әгҖӮ
зЎ®и®ӨвҖңдҪҝиҫ…еҜјдёңе®«вҖқзҡ„еҜ№иұЎдёәеӯҷзҷ»пјҢдёҺеӨҡз§ҚдҪӣж•ҷе…ёзұҚжңүе…іж”Ҝи°ҰвҖңжұүзҢ®жң«д№ұпјҢйҒҝең°дәҺеҗҙвҖқпјҢвҖңеӯҷжқғй—»е…¶еҚҡеӯҰжңүжүҚж…§пјҢеҚіеҸ¬и§Ғд№ӢвҖқзӯүи®°иҪҪпјҢж—¶й—ҙдёҠзӣёдә’з»ҹдёҖгҖӮд№ҹдёҺвҖңй»„еҲқе…ғе№ҙпјҢеҗҙдё»еӯҷжқғдәҺжӯҰжҳҢе»әжҳҢд№җеҜәвҖқзҡ„и®°иҪҪпјҢеңЁдәӢе®һж–№йқўзӣёдә’еҚ°иҜҒгҖӮиҝҳдёҺеҺҶеҸІж–ҮзҢ®еҜ№еӯҷзҷ»жҲҗй•ҝз»ҸеҺҶзҡ„и®°иҪҪе®Ңе…Ёеҗ»еҗҲгҖӮ
гҖҠдёүеӣҪеҝ—гҖӢи®°иҝ°пјҢй»„еҲқдәҢе№ҙпјҢеҚіе…¬е…ғ221е№ҙпјҢеӯҷжқғеҗ‘жӣ№йӯҸз§°иҮЈпјҢжҺҘеҸ—йӯҸе°ҒеҗҙзҺӢз§°еҸ·гҖӮж—¶е№ҙ12еІҒзҡ„еӯҷзҷ»еҗҢиў«жӢңдёәдёңдёӯйғҺе°ҶпјҢе°ҒдёҮжҲ·дҫҜгҖӮеӯҷжқғд»Ҙеӯҷзҷ»е№ҙе№јжҺЁиҫһйӯҸе°ҒзҲөдҪҚдёҚеҸ—гҖӮеҗҢе№ҙпјҢеӯҷжқғз«Ӣеӯҷзҷ»дёәзҺӢеӨӘеӯҗпјҢжһҒйҮҚи§ҶеҜ№д»–зҡ„еҹ№е…»пјҢејҖе§Ӣдёәеӯҷзҷ»йҖүзҪ®еёҲеӮ…гҖӮвҖңйҖүзҪ®еёҲеӮ…пјҢй“Ёз®Җз§ҖеЈ«пјҢд»Ҙдёәе®ҫеҸӢвҖқгҖӮж”Ҝи°Ұж—ўзІҫйҖҡдёӯеӣҪд№Ұе…ёпјҢвҖңеҚҡи§Ҳз»ҸзұҚвҖқжңүвҖңжҷәеӣҠвҖқд№ӢеҗҚпјҢеҸҲдёҚжҳҜеғ§дҫЈиҖҢжҳҜеұ…еЈ«пјҢжҳҜиҘҝеҹҹ移民дёӯзҡ„еӨҙйқўдәәзү©пјҢиў«еӯҷжқғзңӢдёӯйҖүд»Ҙиҫ…еҜјеӨӘеӯҗпјҢд»ҘвҖңе®ҫеҸӢвҖқгҖҒвҖңе®ҫе®ўвҖқиә«д»Ҫиҫ…еҜјдёңе®«дёҚдјҡеј•дәәйқһи®®гҖӮиҷҪ然гҖҠдёүеӣҪеҝ—гҖӢйҮҢи®°иҪҪзҡ„еӯҷзҷ»еёҲеӮ…дёӯжІЎжңүжҸҗеҲ°ж”Ҝи°ҰпјҢдҪҶжҢүгҖҠй«ҳеғ§еҚ·В·йӯҸеҗҙе»әдёҡе»әеҲқеҜәеә·еғ§дјҡгҖӢйҮҢзҡ„иҜҙжі•пјҢжҳҜвҖңз”ҹиҮӘеӨ–еҹҹпјҢж•…еҗҙеҝ—дёҚиҪҪвҖқпјҢдёҺж”Ҝи°Ұзҡ„еӨ–еҹҹдҪӣж•ҷдҝЎеҫ’жңүзӣҙжҺҘе…ізі»гҖӮ
еӯҷзҷ»еҸ—вҖңй»„иҖҒд№ӢжңҜвҖқзҡ„еҪұе“Қ并жү“дёҠеҫҲж·ұзҡ„жҖқжғізғҷеҚ°пјҢдјјд№Һд№ҹеҸҜд»ҘзңӢзқҖж”Ҝи°ҰжӣҫдёәеӨӘеӯҗиҖҒеёҲзҡ„еҸҲдёҖдҪҗиҜҒгҖӮдёңжұүд»ҘжқҘдәә们жҠҠдҪӣж•ҷзңӢдҪңжҳҜй»„иҖҒйҒ“жңҜзҡ„дёҖз§ҚпјҢеӯҷзҷ»дәҺе…¬е…ғ241е№ҙеңЁе»әдёҡеҺ»дё–еүҚзҡ„дёҠеҗҙдё»д№ҰдёӯеҶҷйҒ“пјҡвҖңж„ҝйҷӣдёӢејғеҝҳиҮЈиә«пјҢеүІдёӢжөҒд№ӢжҒ©пјҢдҝ®й»„иҖҒд№ӢжңҜпјҢз¬ғе…»зҘһе…үпјҢеҠ зҫһзҸҚиҶіпјҢе№ҝејҖзҘһжҳҺд№Ӣиҷ‘пјҢд»Ҙе®ҡж— з©·д№ӢдёҡпјҢеҲҷзҺҮеңҹе№ёиө–пјҢиҮЈжӯ»ж— жҒЁд№ҹгҖӮвҖқжҚ®жӯӨдёҚйҡҫзңӢеҮәпјҢеӯҷзҷ»еҜ№вҖңй»„иҖҒд№ӢжңҜвҖқзҡ„жһҒеҠӣжҺЁеҙҮпјҢеҫҲеҸҜиғҪжқҘиҮӘж”Ҝи°Ұиҫ…еҜјдёңе®«жүҖдә§з”ҹзҡ„зӣҙжҺҘеҪұе“ҚгҖӮ
ж”Ҝи°ҰдҪңдёәеӨӘеӯҗеӯҷзҷ»зҡ„иҖҒеёҲпјҢиҝҳдёҺе…¶дёңиҝҒе»әдёҡд»ҘеҗҺзҡ„иЎҢдёәиҪЁиҝ№й«ҳеәҰеҗ»еҗҲгҖӮе…¬е…ғ229е№ҙ8жңҲпјҢеӯҷжқғеңЁжӯҰжҳҢз§°еёқгҖӮгҖҠдёүеӣҪеҝ—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з§Ӣд№қжңҲпјҢжқғиҝҒйғҪе»әдёҡпјҢеӣ ж•…еәңдёҚж”№йҰҶпјҢеҫҒдёҠеӨ§е°ҶеҶӣйҷҶйҖҠиҫ…еӨӘеӯҗзҷ»пјҢжҺҢжӯҰжҳҢз•ҷдәӢгҖӮвҖқеҗҢе№ҙеә•е°ҶйҰ–йғҪиҝҒеҫҖе»әдёҡпјҢдҪҶжӯҰжҳҢд»ҚдҪңдёәйҷӘйғҪпјҢз•ҷеӨӘеӯҗеӯҷзҷ»д»ҘжҺҢз•ҷдәӢпјҢзқҖйҷҶйҖҠиҫ…дҪҗгҖӮдҪңдёәеӯҷзҷ»зҡ„иҖҒеёҲпјҢж”Ҝи°ҰеңЁеҗҙеӣҪиҝҒйғҪе»әдёҡеҗҺ继з»ӯдјҙйҡҸеӯҷзҷ»з•ҷеұ…йҷӘйғҪжӯҰжҳҢгҖӮеҳүзҰҫе…ғе№ҙ(еҚіе…¬е…ғ232е№ҙ)пјҢеӯҷзҷ»ж¬Ўејҹеӯҷиҷ‘еҚ’дәҺе»әдёҡпјҢеӯҷзҷ»еүҚеҫҖе»әдёҡеҗҠдё§пјҢд»ҺжӯӨеңЁе»әдёҡе®ҡеұ…гҖӮж”Ҝи°ҰйҡҸеҗҺд№ҹд»ҺжӯҰжҳҢиҝҒеҫҖе»әдёҡгҖӮ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пјҢж”Ҝи°ҰиҮӘ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дёңиҝҒе»әдёҡзҡ„ж—¶й—ҙпјҢ并дёҚжҳҜдёңеҗҙиҝҒйғҪзҡ„229е№ҙ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еӯҷзҷ»е®ҡеұ…е»әдёҡд»ҘеҗҺзҡ„еҳүзҰҫе…ғе№ҙеҚіе…¬е…ғ232е№ҙгҖӮеңЁжӯӨд№ӢеүҚзҡ„й»„йҫҷдәҢе№ҙпјҢеҚіе…¬е…ғ230е№ҙпјҢз»ҙзҘҮйҡҫе·Із»ҸеҺ»дё–пјҢз«әеҫӢзӮҺд»ҚеңЁжӯҰжҳҢдёҺж”Ҝи°ҰеҗҲиҜ‘гҖҠж‘©зҷ»дјҪз»ҸгҖӢ2еҚ·зӯүз»Ҹдј гҖӮ
е…¬е…ғ232е№ҙеҗҺж”Ҝи°ҰйҡҸеӨӘеӯҗиҝҒеҫҖе»әдёҡпјҢ继з»ӯдҪӣз»Ҹзҝ»иҜ‘е’ҢвҖңиҫ…еҜјдёңе®«вҖқгҖӮиөӨд№Ңеӣӣе№ҙ(е…¬е…ғ241е№ҙ)еӯҷзҷ»жӯ»еҗҺпјҢж”Ҝи°Ұе…ҘиӢҸе·һз©№йҡҶ(жҲ–дҪңвҖңйҡҳвҖқ)еұұпјҢдёҚеҲ°дә”еҚҒеІҒзҡ„ж”Ҝи°Ұд»ҺжӯӨйҡҗеұ…еұұжһ—пјҢдёҚдәӨдё–еҠЎпјҢеҸ—жҢҒдә”жҲ’пјҢиҮіиҖҒжӯ»дәҺеұұдёӯгҖӮиҝҷд№ҹй«ҳеәҰеҗ»еҗҲж”Ҝи°ҰеҒҡиҝҮеӯҷзҷ»иҖҒеёҲзҡ„иЎҢдёәйҖ»иҫ‘гҖӮ
пјҲ6пјүж”Ҝи°ҰеңЁ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зҡ„иҜ‘з»Ҹжҙ»еҠЁ
ж №жҚ®гҖҠдёӯеӣҪдҪӣж•ҷеҸІгҖӢпјҲ任继ж„Ҳдё»зј–пјүзҡ„и®°иҪҪпјҢжұүжң«жңҖжңүеҪұе“Қзҡ„дҪӣж•ҷиҜ‘з»ҸиҖ…пјҢжңүе®үдё–й«ҳе’Ңж”Ҝи°¶пјҢдёӨдәәйғҪжҳҜеӨ–жқҘеғ§дәәгҖӮж”Ҝи°¶жҳҜж”Ҝдә®зҡ„иҖҒеёҲпјҢж”Ҝи°ҰжҳҜж”Ҝдә®зҡ„еӯҰз”ҹгҖӮж”Ҝи°¶гҖҒж”Ҝдә®гҖҒж”Ҝи°ҰйғҪжҳҜйҘұеӯҰд№ӢеЈ«пјҢеҗҺ世并称вҖңдёүж”ҜвҖқпјҢжңүвҖңеӨ©дёӢеҚҡзҹҘпјҢдёҚеҮәдёүж”ҜвҖқд№ӢиҜҙгҖӮ
дёүеӣҪд№ӢеүҚпјҢдҪӣж•ҷзҡ„иҜ‘з»ҸиҖ…дё»иҰҒжҳҜеӨ–жқҘеғ§дәәпјҢеҪ“ж—¶зҡ„иҜ‘з»ҸеҶ…е®№пјҢд№ҹе®Ңе…Ёз”ұеҚ°еәҰдј е…Ҙзҡ„жўөжң¬з»Ҹд№ҰеҶіе®ҡпјҢеҚіеёҰжқҘд»Җд№Ҳз»Ҹд№Ұе°ұзҝ»иҜ‘д»Җд№Ҳз»Ҹд№ҰгҖӮеҪ“ж—¶зҡ„иҜ‘з»Ҹжҙ»еҠЁпјҢеҹәжң¬дёҠд»Ҙзҝ»иҜ‘дёәдё»пјҢи‘—иҝ°е’ҢжіЁйҮҠйғҪжһҒе…¶зЁҖе°‘гҖӮж”Ҝи°ҰжҳҜдёүеӣҪж—¶жңҹжқ°еҮәзҡ„дҪӣз»Ҹзҝ»иҜ‘家пјҢиҖҢдё”жҳҜдёҖеҗҚеұ…еЈ«гҖӮжӯЈжҳҜд»Һж”Ҝи°ҰеңЁжӯҰжҳҢзҡ„иҜ‘з»Ҹжҙ»еҠЁејҖе§ӢпјҢд»ҘеҗҺдҫҝйҖҗжёҗжңүе°‘йҮҸжұүең°еғ§дәәжҲ–еұ…еЈ«еҠ е…ҘеҲ°дҪӣж•ҷиҜ‘з»Ҹд№ӢдёӯпјҢдҪҝдҪӣж•ҷеңЁзӨҫдјҡдёҠеҫ—еҲ°жӣҙе№ҝжіӣдј ж’ӯгҖӮ
ж”Ҝи°ҰиҜ‘з»Ҹзҡ„еҶ…е®№еӨҡдёәеӨ§д№ҳдҪӣе…ёпјҢжңүе°‘ж•°е°Ҹд№ҳдҪӣе…ёзҡ„зҝ»иҜ‘гҖӮ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жҳҜе°Ҹд№ҳдҪӣж•ҷзҡ„еҹәжң¬иҜ»зү©пјҢе…ҲеҗҺеңЁдёӯеӣҪиҮіе°‘жңүе…ӯдёӘиҜ‘жң¬гҖӮ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жі•еҸҘз»ҸеәҸ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еҲ«жңүж•°йғЁпјҢжңүд№қзҷҫеҒҲпјҢжҲ–дёғзҷҫеҒҲпјҢеҸҠдә”зҷҫеҒҲгҖӮвҖқвҖңиҝ‘дё–и‘ӣж°ҸпјҢдј дёғзҷҫеҒҲгҖӮвҖқд№ҹе°ұжҳҜиҜҙеңЁж”Ҝи°Ұе’Ңз»ҙзҘҮйҡҫгҖҒз«әе°ҶзӮҺеҗҲдҪңиҜ‘еҮә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д»ҘеүҚпјҢдёӯеӣҪе·ІжңүеҲқиҜ‘дҪҶе·ІдҪҡж•Јзҡ„дёғзҷҫеҒҲжң¬гҖӮй»„жӯҰдёүе№ҙ(е…¬е…ғ224е№ҙ)пјҢдә”зҷҫеҒҲжң¬зҡ„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жўөжң¬з”ұз»ҙзҘҮйҡҫеёҰе…ҘжӯҰжҳҢпјҢйҡҸеҗҺдёүдәәеҗҲдҪңиҜ‘еҮәзҡ„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дәҢеҚ·пјҢжҳҜ第дәҢиҜ‘зҡ„дә”зҷҫеҒҲжң¬гҖӮеҗҺжқҘж”Ҝи°Ұи®ӨдёәиҮӘе·ұдёҺз»ҙзҘҮйҡҫгҖҒз«әе°ҶзӮҺзҡ„еҗҲиҜ‘жң¬вҖңиҜ‘жүҖдёҚи§ЈпјҢеҲҷзјәдёҚдј пјҢж•…жңүи„ұеӨұвҖқпјҢдәҺжҳҜеҚ•зӢ¬еҶҚдәҲдҝ®и®ўпјҢеҫ—еҗҙиҜ‘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2еҚ·жң¬пјҢд№ҹжҳҜдёӯеӣҪзҺ°еӯҳжөҒдј жңҖе№ҝзҡ„йҖҡиЎҢжң¬гҖӮ
ж”Ҝи°Ұзҝ»иҜ‘зҡ„д»ЈиЎЁжҖ§з»Ҹдј пјҢжңүгҖҠз»ҙж‘©иҜҳз»ҸгҖӢ2 еҚ·гҖҒгҖҠеӨ§иҲ¬жіҘжҙ№з»ҸгҖӢ2еҚ·гҖҒгҖҠжҳҺеәҰз»ҸгҖӢ4еҚ·гҖҒгҖҠжі•еҸҘз»ҸгҖӢ2еҚ·гҖҒгҖҠйҰ–жҘһдёҘз»ҸгҖӢ2еҚ·гҖҒгҖҠжҳҺеәҰз»ҸгҖӢ4еҚ·гҖҒгҖҠйҳҝејҘйҷҖз»ҸгҖӢ2еҚ·гҖҒгҖҠз‘һеә”жң¬иө·з»ҸгҖӢ2еҚ·гҖҒгҖҠж…§еҚ°з»ҸгҖӢ1еҚ·гҖҒгҖҠжң¬дёҡз»ҸгҖӢ1еҚ·гҖҒгҖҠжі•й•ңз»ҸгҖӢ2еҚ·гҖҒгҖҠжӮ”иҝҮз»ҸгҖӢ1еҚ·гҖҒгҖҠд№үи¶із»ҸгҖӢ2еҚ·гҖҒгҖҠдәҶжң¬з”ҹжӯ»з»ҸгҖӢ1еҚ·гҖҒгҖҠе”ҜжҳҺдәҢеҚҒеҒҲгҖӢ1еҚ·гҖҒгҖҠеҚҒдәҢй—ЁеӨ§ж–№з»ҸгҖӢ1еҚ·зӯү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ж”Ҝи°ҰиҝҳжҠҠиҮӘиҜ‘зҡ„гҖҠеҫ®еҜҶзү№з»ҸгҖӢдёҺгҖҠйҷҖйӮ»е°јз»ҸгҖӢ(еӨұиҜ‘)гҖҒгҖҠжҖ»жҢҒз»ҸгҖӢ(еӨұиҜ‘)2 з»ҸеҗҲдёә1жң¬пјҢжҲҗдёәдҪӣз»Ҹзҝ»иҜ‘дјҡиҜ‘зҡ„ејҖз«ҜпјҢдёәдҪӣе…ёзҡ„зҝ»иҜ‘гҖҒдҪӣеӯҰзҡ„ж’ӯжү¬дҪңеҮәдәҶйҮҚиҰҒиҙЎзҢ®гҖӮжҚ®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еҚ·дәҢ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ж”Ҝи°Ұд»Ҙеҗҙдё»еӯҷжқғй»„жӯҰеҲқ(е…¬е…ғ222е№ҙ)иҮіеӯҷдә®е»әе…ҙдёӯ(зәҰе…¬е…ғ253е№ҙ)пјҢе…ұиҜ‘з»Ҹ36йғЁ48еҚ·вҖқгҖӮиҝҷдёӘж•°еӯ—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ж”Ҝи°Ұдј гҖӢи®°дҪң27йғЁгҖҒгҖҠй«ҳеғ§еҚ·В·йӯҸеҗҙе»әдёҡе»әеҲқеҜәеә·еғ§дјҡгҖӢи®°дҪң49йғЁгҖӮиҝҷжҳҜж”Ҝи°ҰеңЁжӯҰжҳҢ(й„Ӯе·һ)е’Ңе»әдёҡ(еҚ—дә¬)дёӨеӨ„иҜ‘з»Ҹзҡ„жҖ»ж•°пјҢе…·дҪ“еңЁжӯҰжҳҢеҸҠе»әдёҡеҲҶеҲ«иҜ‘з»ҸеӨҡе°‘е№¶ж— з»ҶеҲҶи®°иҪҪгҖӮдёҚиҝҮд»Һж—¶й—ҙдёҠиҖғжөӢпјҢж”Ҝи°ҰеңЁжӯҰжҳҢиҜ‘з»Ҹзҡ„ж—¶й—ҙзәҰеҚ дёүеҲҶд№ӢдёҖпјҢеңЁе»әдёҡжҺҘиҝ‘дёүеҲҶд№ӢдәҢгҖӮ
ж”Ҝи°ҰеҲӣдҪңе”ұиөһ(жўөе‘—)пјҢејҖдҪӣж•ҷйҹід№җдј е…ҘжұҹеҚ—д№Ӣе…ҲжІігҖӮгҖҠжі•иӢ‘зҸ жһ—В·жўөиҙқзҜҮгҖӢиҜҙпјҡвҖңеҜ»иҘҝж–№(еҚ°еәҰ)д№Ӣжңүе‘—пјҢзҠ№дёңеӣҪд№ӢжңүиөһгҖӮиөһиҖ…пјҢд»Һж–Үд»Ҙз»“йҹі;иҙқиҖ…пјҢзҹӯеҒҲд»ҘжөҒйўӮгҖӮжҜ”е…¶дәӢд№үпјҢеҗҚејӮе®һеҗҢгҖӮжҳҜж•…з»ҸиЁҖпјҢд»Ҙеҫ®еҰҷйҹіеЈ°жӯҢиөһдәҺдҪӣеҫ·пјҢж–Ҝд№Ӣи°“д№ҹгҖӮвҖқеҸҜи§Ғе”ұиөһжҳҜеңЁд№җеҷЁдјҙеҘҸдёӢжј”е”ұзҡ„иҜ—еҒҲпјҢдёҖиҲ¬иў«е®үжҸ’еңЁиғҢиҜө(иҪ¬иҜ»)дҪӣз»Ҹзҡ„ж—¶еҖҷиҝӣиЎҢгҖӮж—©жңҹдҪӣж•ҷйҹід№җдҪңе“Ғжңүж”Ҝи°ҰеҲӣдҪңзҡ„е”ұиөһгҖҠиөһиҸ©иҗЁиҝһеҸҘжўөе‘—гҖӢзӯүгҖӮ
дёүеӣҪеҲқжңҹеңЁжӯҰжҳҢпјҢиҜ‘з»Ҹе·ҘдҪңд»ҺеӨҙејҖе§ӢпјҢеҗ„и·ҜиҜ‘з»ҸиҖ…зҡ„еӯҰиҜҶж°ҙе№ігҖҒжҖқжғіеўғз•ҢдёҚе°ҪзӣёеҗҢпјҢиҜ‘еҮәзҡ„з»Ҹдј йҡҫе…ҚеӯҳеңЁеҗ„з§Қе·®ејӮгҖӮж”Ҝи°ҰзІҫйҖҡеӨҡеӣҪиҜӯиЁҖпјҢд»–зҡ„зҝ»иҜ‘еҫҖеҫҖиғҪеңЁеҗ„з§ҚйЈҺж јзҡ„иҜ‘ж–ҮдёӯеҜ»жұӮеҲ°еҮҶзЎ®з®ҖзӮјзҡ„иЎЁиҫҫгҖӮ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ж”Ҝи°Ұзҡ„еұ…еЈ«иә«д»ҪдҪҝе…¶дҪӣж•ҷжҙ»еҠЁдёҚд»…д»…йҷҗдәҺдҪӣеҜәжҲ–еҗҙйғҪзҡ„дёҠеұӮзӨҫдјҡпјҢиҖҢжҳҜйҖҡиҝҮеұ…еЈ«зҡ„е№ҝжіӣз”ҹжҙ»жҺҘи§ҰжңүжӣҙеӨҡжңәдјҡи®©дҪӣж•ҷеңЁзӨҫдјҡеҗ„ж–№йқўгҖҒзү№еҲ«жҳҜеңЁжҷ®йҖҡиҖҒзҷҫ姓дёӯдј ж’ӯгҖӮдёүеӣҪж—©жңҹжӯҰжҳҢең°еҢәе»әжҲҗжҳҢд№җеҜәд»ҘеҗҺпјҢжҺҘзқҖеҸҲе»әиө·ж…§е®қеҜәдёҺе®қе®ҒйҷўпјҢеҚ°еәҰеғ§дәәз»ҙзҘҮйҡҫе’Ңз«әеҫӢзӮҺз»“дјҙж…•еҗҚжқҘеҲ°жӯҰжҳҢпјҢиҝҷдәӣйғҪжҜ”еә·еғ§дјҡвҖңиөӨд№ҢеҚҒе№ҙпјҲе…ідәҺ247е№ҙпјүвҖқеҲ°е»әдёҡгҖҒ然еҗҺеӯҷжқғдёәе…¶ж–°е»әе»әеҲқеҜәж—©дәҶдәҢеҚҒеӨҡе№ҙгҖӮ
дёүеӣҪж—¶жңҹдҪӣж•ҷеңЁ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ең°еҢәзҡ„е№ҝжіӣдј ж’ӯпјҢд»ҺеҪ“д»ЈиҖғеҸӨеҸ‘зҺ°дёӯд№ҹиғҪеҫ—еҲ°еҫҲеҘҪзҡ„иҜҒжҳҺгҖӮ
дёҠдё–зәӘ80е№ҙд»ЈеҲқпјҢеҚ—дә¬еӨ§еӯҰж•ҷжҺҲи’ӢиөһеҲқеңЁгҖҠж№–еҢ—й„ӮеҹҺе…ӯжңқиҖғеҸӨзҡ„дё»иҰҒ收иҺ·гҖӢдёҖж–Үдёӯ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еңЁй„ӮеҹҺе…ӯжңқеў“зҡ„йҡҸ葬е“ҒдёӯпјҢе…ұеҸ‘зҺ°7件жңүе…ідҪӣж•ҷзҡ„йҒ—зү©пјҢе…¶дёӯ3件жҳҜй“ңй•ңпјҢ4件жҳҜйҷ¶з“·еҷЁгҖӮ3件й“ңй•ңйғҪеұһдәҺжҹҝи’Ӯиҝһеј§еӨ”еҮӨй•ңпјҢеҰӮM4009пјҡ2пјҢзӣҙеҫ„дёә16еҺҳзұіпјҢеӣӣи’ӮеҶ…еҲҶеҲ«еЎ«д»ҘйҫҷгҖҒиҷҺгҖҒй№ҝгҖҒ马пјҢиҝһеј§еҶ…дёәеҸҳејӮж¶Ўдә‘зә№пјҢиҫ№йҘ°дёәдҪңеҘ”и…ҫи·іи·ғзҠ¶зҡ„зҸҚзҰҪе’Ңз‘һе…ҪпјҢдёӯеӨ№жңүдёӨиәҜе§ҝжҖҒйЈҳйҖёзҡ„вҖңйЈһеӨ©вҖқеғҸпјҢжӯӨеў“еә”еұһеӯҷеҗҙжҷҡжңҹеў“гҖӮеҗҢдёҖеў“ең°M4037жүҖеҮәзҡ„еҗҢеһӢй•ңдёӯдәҰжңүдёҖ件дҪӣеғҸй•ңпјҢзӣҙеҫ„дёә16.3еҺҳзұіпјҢеӣӣи’ӮеҶ…зҡҶжңүдҪӣеғҸпјҢе…¶дёӯдёүи’Ӯдёӯзҡ„дҪӣеғҸеқҮдҪңз»“и·Ҹи·ҢеқҗзҠ¶пјҢдёҠжңүеҚҺзӣ–пјҢйЎ¶жңүиӮүй«»пјҢиғҢжңүйЎ№е…үпјҢе…¶иҺІеә§дёӨдҫ§еҗ„жңүдёҖжҠӨжі•зҘһйҫҷ;еҸҰдёҖи’ӮеҶ…дёәдёҖдҪӣдҫ§еқҗдәҺиҺІеә§дёҠпјҢж—Ғз«ӢдёҖдҫҚиҖ…жҢҒжӣІжҹ„еҚҺзӣ–пјҢеүҚи·ӘдёҖдәәдҪңзӨјдҪӣзҠ¶;и’Ӯй—ҙдёәеӣӣз»„еҸЈиЎ”д»Әд»—зҡ„иӮүеҮӨеӣҫжЎҲпјҢиҝһеј§еӨ–зҡ„иҫ№йҘ°дәҰдёәзҸҚзҰҪе’Ңз‘һе…ҪгҖӮиҝҳжңүдёҖ件йҮҮйӣҶиҖҢжқҘзҡ„еҗҢеһӢй•ңпјҢзӣҙеҫ„дёә14.2еҺҳзұіпјҢдёүи’ӮеҶ…еҗ„жңүдёҖе…ҪпјҢеҸҰдёҖи’ӮеҶ…жңүжҲҙй«ҳеҶ гҖҒи“„й•ҝйЎ»гҖҒдҫ§еқҗдәҺиҺІеә§дёҠзҡ„дәәзү©пјҢжҲ–зі»дҪӣж•ҷдёӯзҡ„еұ…еЈ«еғҸ;и’Ӯй—ҙдёәеӣӣз»„еҸЈиЎ”绶еёҰзҡ„еҜ№еҮӨеӣҫжЎҲпјҢиҝһеј§еӨ–зҡ„иҫ№йҘ°дёәжңұйӣҖгҖҒеӨ©й№ҝзӯүзҸҚзҰҪе’Ңз‘һе…ҪгҖӮ4件дёҺдҪӣж•ҷжңүе…ізҡ„йҷ¶з“·гҖӮе…¶дёӯйҷ¶дҝ‘зҡ„зңүй—ҙдјјжңүвҖңзҷҪжҜ«зӣёвҖқпјҢзұ»дјјжӯҰжҳҢж°ёе®үдә”е№ҙеў“е’Ңй•ҝжІҷж°ёе®ҒдәҢе№ҙеў“жүҖеҮәзҡ„еҗҢзұ»дҝ‘пјҢеҮәиҮӘиҘҝеұұеҗҙеў“дёӯгҖӮйқ’з“·дҪӣеғҸзҶҸеҮәеңҹдәҺиҘҝеұұеҚ—йә“зҡ„еӯҷе°ҶеҶӣеў“вҖқгҖӮ
й„Ӯе·һеёӮеҚҡзү©йҰҶзҶҠеҜҝжҳҢеңЁгҖҠжұүдёүеӣҪж—¶жңҹжӯҰжҳҢдҪӣж•ҷж–ҮеҢ–йҒ—еӯҳгҖӢдёҖж–Үдёӯд№ҹд»Ӣз»ҚпјҡвҖң1992е№ҙ12жңҲпјҢж№–еҢ—зңҒй„Ӯе·һеёӮзІ®йЈҹйғЁй—ЁеңЁеёӮеҢәеҚ—йғЁзҡ„еЎҳи§’еӨҙдҝ®е»әзІ®жІ№д»“еә“ж—¶пјҢеҸ‘зҺ°еҮ еә§еҗҙжҷӢж—¶жңҹзҡ„墓葬гҖӮж№–еҢ—зңҒиҖғеҸӨз ”з©¶жүҖдјҡеҗҢй„Ӯе·һеёӮеҚҡзү©йҰҶзҡ„иҖғеҸӨдәәе‘ҳеҜ№иҝҷдәӣ墓葬иҝӣиЎҢдәҶеҸ‘жҺҳпјҢеңЁе…¶дёӯзҡ„еӣӣеҸ·еў“дёӯеҸ‘зҺ°дәҶдёҖе°Ҡйқ’з“·дҪӣеғҸгҖӮиҝҷдёҖе°ҠдҪӣдёәзӢ¬з«Ӣзҡ„дҪӣеғҸпјҢйҷӨеә•еә§еӨ–пјҢйҖҡдҪ“ж–ҪжңүиӨҗиүІзҡ„йҮүгҖӮйҖҡй«ҳ20еҺҳзұіпјҢиӮ©е®Ҫ9.8еҺҳзұігҖӮдҪӣеғҸзӣҳи…ҝпјҢеқҗеңЁдёҖиҝ‘дјјдәҺж–№еҪўзҡ„е№іеҸ°дёҠпјҢиә«зқҖйҖҡиӮ©иЎЈпјҢиғёеүҚжңүдә”йҒ“вҖңUвҖқеҪўиЎЈзә№пјҢи…№йғЁдәҰжңүж•°йҒ“зӣёеҗҢзҡ„иЎЈзә№пјҢеӨҙйЎ¶жңүйҡҶиө·зҡ„иӮүй«»пјҢеҸҢжүӢиў«иЎЈзү©йҒ®зӣ–пјҢе№іж”ҫдәҺеҸҢиҶқдёҠпјҢжүӢејҸдёҚжҳҺгҖӮйҖҡиҝҮеҜ№е…ұеӯҳзү©(йҷ¶з“·зҡ„зЈЁгҖҒд»“гҖҒйёЎгҖҒйёӯзӯүжҳҺеҷЁ)зҡ„еҲҶжһҗпјҢиҜҒжҳҺиҝҷжҳҜдёҖеә§еӯҷеҗҙж—¶жңҹзҡ„墓葬гҖӮвҖқ
еӨ§йҮҸдёңеҗҙж—¶жңҹзҡ„еҸӨ墓葬иҖғеҸӨеҸ‘зҺ°иЎЁжҳҺпјҢеӣ дёәж”Ҝи°ҰзӯүдәәдёүеӣҪж—©жңҹеңЁжӯҰжҳҢзҡ„иҜ‘з»Ҹж’ӯж•ҷжҙ»еҠЁпјҢдёҚд»…дҪҝ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ең°еҢәзҡ„дҪӣж•ҷдј ж’ӯеңЁдёңеҗҙж—¶жңҹе°ұе·Із»ҸеҲқ具规模пјҢеҗҢж—¶д№ҹеҜ№дҪӣж•ҷз”ұе®«е»·дј е…ҘзӨҫдјҡгҖҒиҝӣиҖҢеҜ№жҷ®йҖҡзҷҫ姓з”ҹжҙ»дә§з”ҹеҪұе“ҚпјҢеҗ‘еүҚеӨ§еӨ§жҺЁиҝӣдәҶдёҖжӯҘгҖӮ
2гҖҒдёңжҷӢж…§иҝңеңЁиҘҝеұұдҝ®иЎҢ
дҪӣж•ҷиҮӘжұүжң«иҮідёүеӣҪеҲқжңҹдј е…ҘеҚ—ж–№пјҢеҲ°дёӨжҷӢеҚ—еҢ—жңқж—¶жңҹе·ІжңүдәҶеҫҲеӨ§зҡ„еҸ‘еұ•гҖӮгҖҠж№–еҢ—ж–ҮеҢ–еҸІ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жҳҜдҪӣж•ҷеҲқдј ж№–еҢ—зҡ„иө·жӯҘйҳ¶ж®өпјҢеҜ№дёӯеӣҪдҪӣж•ҷзҡ„еҪұе“ҚеңЁдәҺиҜ‘з»Ҹпјӣй„Ӯе·һд»ҘеҗҺпјҢиҘ„йҳіеӣ дёәжңүйҒ“е®үзҡ„жҙ»еҠЁпјҢдҪӣж•ҷж’ӯжү¬дёҖж—¶иҪ°иҪ°зғҲзғҲпјҢдҪҶйҡҸзқҖж”ҝеұҖеҸҳеҢ–пјҢиҘ„йҳідҪӣж•ҷ移еёҲдәҺеҸӨеҹҺжұҹйҷөгҖӮвҖқгҖӮ
е…¬е…ғ4дё–зәӘдёӯеҸ¶д»ҘеҗҺпјҢдҪӣж•ҷеңЁд»ҠеӨ©зҡ„ж№–еҢ—ең°еҹҹд»ЈиЎЁжҖ§дәәзү©жҳҜйҒ“е®үпјҢж…§иҝңжҳҜйҒ“е®үзҡ„й«ҳеҫ’гҖӮе…¬е…ғ378е№ҙпјҢж…§иҝңйҒөеҙҮеёҲе‘ҪпјҢзҺҮејҹеӯҗж•°еҚҒдәәиҮӘиҘ„йҳіеҚ—дёӢж¬ІеҫҖе№ҝдёңзҪ—жө®еұұгҖӮдёҖи·ҜдёҠе…ҲиҮіиҚҶе·һдҪҸдёҠжҳҺеҜәпјҢе…¬е…ғ379е№ҙйЎәжұҹиҖҢдёӢеңЁжӯҰжҳҢд№…еұ…пјҢдәҺиҘҝеұұдҝ®иЎҢпјҢиҮіе…¬е…ғ381е№ҙеҫҖжө”йҳіеәҗеұұдёңжһ—еҜәгҖӮ
пјҲ1пјүй«ҳеғ§ж…§иҝң
ж…§иҝң(е…¬е…ғ334е№ҙ-е…¬е…ғ416е№ҙ)пјҢдҝ—姓иҙҫпјҢйӣҒй—ЁйғЎжҘјзғҰеҺҝ(д»ҠеұұиҘҝеҺҹе№і)дәәгҖӮеҮәз”ҹдәҺдё–д»Јд№ҰйҰҷд№Ӣ家пјҢд»Һе°Ҹиө„иҙЁиҒӘйў–пјҢеӢӨжҖқж•ҸеӯҰгҖӮеҚҒдёүеІҒйҡҸиҲ…зҲ¶д»ӨзӢҗж°ҸжёёеӯҰжҙӣйҳігҖҒи®ёжҳҢдёҖеёҰпјҢвҖңеҚҡз»је…ӯз»ҸгҖҒе°Өе–„иҖҒеә„вҖқгҖӮдәҢеҚҒдёҖеІҒж—¶дёҺејҹејҹж…§жҢҒеӣ йҒҝжҲҳд№ұиҮіжҒ’еұұпјҢжҠ•й«ҳеғ§йҒ“е®үй—ЁдёӢпјҢй’»з ”дҪӣж•ҷвҖңиҲ¬иӢҘжҖ§з©әвҖқеӯҰгҖӮз”ұжӯӨи®ӨдёәвҖңе„’йҒ“д№қжөҒпјҢзҡҶзі жһҮиҖівҖқгҖӮйҒӮиҲҚдҝ—еҮә家пјҢд»ҺйҒ“е®үдҝ®иЎҢгҖӮ
е…¬е…ғ365е№ҙпјҢеӣ ж—¶еұҖеҠЁиҚЎпјҢж…§иҝңйҡҸйҒ“е®үеҚ—дёӢиҘ„йҳігҖӮгҖҠй«ҳеғ§еӮіВ·жҷӢеәҗеұұйҮҠж…§иҝң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е…¬е…ғ378е№ҙпјҢвҖңйҒ“е®үдёәжңұеәҸжүҖжӢҳпјҢдёҚиғҪеҫ—еҺ»пјҢд№ғеҲҶеј еҫ’дј—пјҢеҗ„йҡҸжүҖд№ӢгҖӮдёҙи·ҜпјҢиҜёй•ҝеҫ·зҡҶиў«иҜІзәҰпјҢиҝңдёҚи’ҷдёҖиЁҖгҖӮиҝңд№ғи·Әжӣ°пјҡзӢ¬ж— и®ӯеӢ–пјҢжғ§йқһдәәдҫӢ?е®үжӣ°пјҡеҰӮжұқиҖ…пјҢеІӮеӨҚзӣёеҝ§?вҖқж„ҸжҖқжҳҜиҜҙпјҢеғҸдҪ иҝҷж ·зҡ„дәәпјҢиҝҳйңҖиҰҒжӢ…еҝғеҗ—?еҸҜи§ҒйҒ“е®үеҜ№ж…§иҝңзҡ„дҪӣеӯҰйҖ иҜЈйқһеёёиӮҜе®ҡгҖӮ
ж…§иҝңзҺҮејҹеӯҗж•°еҚҒдәәеҚ—дёӢпјҢе…ҲиҮіиҚҶе·һзҹӯдҪҸдёҠжҳҺеҜәгҖӮ379е№ҙеҲқпјҢдёәе®һзҺ°еёҲзҲ¶вҖңдҪҝйҒ“жөҒдёңеӣҪпјҢе…¶еңЁиҝңд№ҺвҖқзҡ„жңҹжңӣпјҢж…§иҝңзҰ»ејҖдёҠжҳҺеҜәйЎәжұҹдёңдёӢпјҢйҖ”з»ҸжӯҰжҳҢж—¶и§ҒжЁҠеұұи‘ұйғҒпјҢдёҙжұҹиҖёз«ӢпјҢйҒӮиҲҚиҲҹзҷ»еІёпјҢеҫӘжәӘиҖҢдёҠпјҢз•ҷдҪҸеңЁеҜ’жәӘеҜәгҖӮеӣ еҫ—йҷ¶дҫғиө еҜ’жәӘеҜә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йҮ‘еғҸпјҢеҸҲиҫҹеҗҙзҺӢеӯҷжқғйҒҝжҡ‘е®«ж•…еҹәпјҢеңЁеҜ’жәӘд№ӢдёҠе»әиҘҝеұұеҜәгҖӮеұ…жӯҰжҳҢдёӨе№ҙпјҢејҳжі•еёғж•ҷпјҢйҒҚи®ҝз»Ҹдј пјҢеҝ—еҝғеҮҖеңҹпјҢжӮүеҝғдҝ®иЎҢгҖӮ
е…¬е…ғ381е№ҙпјҢж…§иҝңеҲ°жұҹиҘҝеәҗеұұеҫҖи§ҒеёҲејҹж…§ж°ёпјҢеҫ—жұҹе·һеҲәеҸІжЎ“дјҠеҠ©е»әдёңжһ—еҜә并е°ұжӯӨе®ҡеұ…гҖӮжӯӨеҗҺдёүеҚҒдҪҷе№ҙй—ҙпјҢж…§иҝңеҪұдёҚеҮәеұұпјҢиҝ№дёҚе…Ҙдҝ—пјҢз»“зӨҫдҝ®иЎҢгҖӮе…¬е…ғ402е№ҙпјҢж…§иҝңдёҺеҲҳйҒ—ж°‘зӯүдёҖзҷҫдәҢеҚҒдёүдәәпјҢеңЁеәҗеұұиҲ¬иӢҘеҸ°зІҫиҲҚж— йҮҸеҜҝдҪӣеғҸеүҚе»әж–ӢеҸ‘иӘ“пјҢдј—зӯүйҪҗеҝғжҪңдҝ®еҮҖеңҹжі•й—ЁпјҢд»Ҙжңҹе…ұз”ҹиҘҝж–№жһҒд№җдё–з•ҢгҖӮжӯӨж¬ЎйӣҶдјҡеүҚпјҢеӨ§еёҲжӣҫзҺҮдј—дәҺдёңжһ—еҜәеүҚеҮҝжұ з§ҚжӨҚзҷҪиҺІпјҢжҳҜд»ҘдёӯеӣҪдҪӣж•ҷеҸІдёҠз§°жӯӨйӣҶз»“дёәвҖңз»“зҷҪиҺІзӨҫвҖқпјҢжҲ–з®Җз§°вҖңз»“иҺІзӨҫвҖқгҖӮеҮҖеңҹе®—еӣ жӯӨеҸҲз§°дёәвҖңиҺІе®—вҖқгҖӮ
е…¬е…ғ416е№ҙпјҢж…§иҝңз»ҲиҖҒдәҺеәҗеұұгҖӮеҮҖеңҹдёҖж•ҷе®Ӣе…ғеҗҺз«Ӣе®—пјҢж…§иҝңиў«е…¬и®ӨдёәдҪӣж•ҷеҮҖеңҹе®—е§ӢзҘ–
пјҲ2пјүиҘҝеұұдҝ®иЎҢ
ж…§иҝңйҖ”з»ҸжӯҰжҳҢ并еұ…з•ҷиҘҝеұұдёӨе№ҙжңүдҪҷпјҢжё…д№ҫйҡҶ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ж…§иҝңвҖңйҡҸе®ү(йҒ“е®ү)еҚ—жёёиҘ„йҳіпјҢеұ…иҚҶе·һдёҠжҳҺеҜәпјҢиҮіжө”йҳійҒ“з»ҸжӯҰжҳҢпјҢи§Ғеұұж°ҙжё…з§ҖпјҢеҸҜд»ҘжҒҜеҝғпјҢеӣ жһ„еҜ’жәӘзІҫиҲҚпјҢеұ…д№…д№ӢпјҢеӨҚеҺ»еҜ’жәӘпјҢиҜЈеәҗеұұгҖӮвҖқп№қиҝҷж®өж–Үеӯ—и®°иҝ°дәҶж…§иҝңеұ…з•ҷжӯҰжҳҢзҡ„еӨ§иҮҙз»ҸиҝҮгҖӮйҖ”з»ҸжӯҰжҳҢпјҢи§ҒиҘҝеұұеұұж°ҙжё…з§ҖпјҢдәҺеҜ’жәӘзІҫиҲҚд№…еұ…пјҢеҗҺзҰ»ејҖеҜ’жәӘеҺ»еҫҖеәҗеұұ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иҝҷж®өж–Үеӯ—еҜ№ж…§иҝңжӯҰжҳҢеұ…з•ҷзҡ„е…·дҪ“ж—¶й—ҙгҖҒзү№еҲ«жҳҜд№…еұ…жӯҰжҳҢзҡ„дё»иҰҒжҙ»еҠЁпјҢе®Ңе…ЁжІЎжңүжҸҗеҸҠгҖӮ
ж…§иҝңдёәдҪ•д№…еұ…жӯҰжҳҢпјҹд»ҠеӨ©е·Із»Ҹж— д»ҺжҸЈжөӢгҖӮдҪҶжҚ®дҪӣж•ҷе…ёзұҚе’ҢеҸӨд»ЈжӯҰжҳҢең°ж–№еҸІеҝ—зҡ„зӣёе…іи®°иҪҪпјҢж…§иҝңеұ…жӯҰжҳҢжңҹй—ҙжүҖдёәдёүдәӢпјҢжҲ–и®ёеҸҜд»ҘйғЁеҲҶи§ЈејҖдёҠиҝ°з–‘й—®гҖӮ
и®ҝдҪӣж•ҷз»ҸеҚ·гҖӮж…§иҝңиҮӘд»ҺйҒ“е®үжі•еёҲеҸ—дёҡд»ҘжқҘпјҢеҚід»ҘеӨ§жі•дёәе·ұд»»пјҢжңүж„ҹдәҺеҪ“ж—¶з»Ҹе…ёжңӘеӨҮпјҢеҫӢи—Ҹж®ӢзјәпјҢзү№еҲ«жіЁж„ҸжҗңйӣҶдҪӣж•ҷз»ҸеҚ·гҖӮ
жҷӢд»ЈжӯҰжҳҢпјҢжҳҜжұүжң«дёүеӣҪеҲқжңҹдҪӣж•ҷдј е…ҘжұҹеҚ—жңҖеҲқзҡ„еҹәең°пјҢжӣҫз»Ҹеҗёеј•дј—еӨҡеӨ–жқҘеғ§дәәе’ҢиҜ‘з»ҸеӨ§еёҲеңЁиҝҷйҮҢиҜ‘з»Ҹдј ж•ҷгҖӮиҝҷйҮҢжӣҫз»ҸжҳҜ60е№ҙзҡ„еҗҙеӣҪйҰ–йғҪгҖҒйҷӘйғҪпјҢеҸҲжҳҜдёӨжҷӢеҶӣдәӢйҮҚй•ҮпјҢеўғеҶ…дёҚд»…жӢҘжңүжҳҢд№җеҜәгҖҒжғ е®қеҜәгҖҒе®қе®ҒйҷўгҖҒеҜ’жәӘеҜәзӯүеӨҡеә§зҷҫе№ҙеҜәйҷўпјҢиҖҢдё”жңүеҪұе“Қзҡ„дҪӣж•ҷжҙ»еҠЁдёҚж–ӯпјҢеҰӮйҷ¶дҫғеҗ‘еҜ’жәӘеҜәйҖҒеғҸгҖҒжҲҙжёҠдёәжҳҢд№җеҜәдҪңи®°гҖҒи°ўе°ҡеңЁжҳҢд№җеҜәз«ӢзҹізӯүзӯүпјҢиҜҙжҳҺдҪӣж•ҷеңЁжӯҰжҳҢзӨҫдјҡеҗ„йўҶеҹҹеҗ„йҳ¶еұӮе…·жңүе№ҝжіӣеҹәзЎҖпјҢиҮӘ然少дёҚдәҶдҪӣж•ҷз»Ҹе…ёи—ҸдәҺеҜәйҷўз”ҡиҮіж°‘й—ҙгҖӮж…§иҝңеҚ—иҝҒжқҘеҲ°жӯҰжҳҢпјҢжҡӮдҪҸеңЁвҖңеҜ’жәӘзІҫиҲҚвҖқпјҢжӯӨеӨ„еҲҡеҲҡз»ҸеҺҶиҝҮдёҖеңәеӨ§зҒ«пјҢд№ӢеүҚзҡ„еҜ’жәӘеҜәвҖңеҜәж—ўз„ҡе°ҪпјҢе”ҜеғҸеұӢеӯҳз„үвҖқгҖӮж…§иҝңеңЁвҖңеҫ—йҷ¶дҫғиө еҜ’жәӘеҜә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йҮ‘еғҸвҖқ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ж·ұдёәйҒӯеӨ§зҒ«з„ҡе°Ҫзҡ„еҜәи—Ҹз»ҸеҚ·жғӢжғңпјҢеҗҢж—¶д№ҹжӣҙеўһеҠ дәҶдәҺеҪ“ең°и®ҝеҜ»з»ҸеҚ·зҡ„зҙ§иҝ«ж„ҹгҖӮеҗ‘жқҘд»ҘеӨ§жі•дёәе·ұд»»пјҢйҒҚйӣҶдҪӣж•ҷз»ҸеҚ·зҡ„ж…§иҝңпјҢдёҚеҸҜиғҪй”ҷиҝҮеңЁиҝҷйҮҢи®ҝйӣҶдҪӣж•ҷз»ҸеҚ·зҡ„еӨ§еҘҪжңәйҒҮпјҢд№…еұ…жӯҰжҳҢиҝҷиҮӘ然жҳҜйҮҚиҰҒзӣ®зҡ„гҖӮ
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ж…§иҝңжі•еёҲеҚ·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еҲқе…ідёӯиҜ‘еҮәеҚҒиҜөпјҢжүҖдҪҷдёҖеҲҶжңӘз«ҹпјҢиҖҢеј—иӢҘеӨҡзҪ—дәЎпјҢиҝңеёёж…Ёе…¶жңӘеӨҮпјҢеҸҠй—»жҳҷж‘©жөҒж”Ҝе…Ҙз§ҰпјҢд№ғйҒ—д№ҰзҘҲиҜ·пјҢд»ӨдәҺе…ідёӯжӣҙеҮәдҪҷеҲҶгҖӮж•…еҚҒиҜөдёҖйғЁпјҢе…·и¶іж— йҳҷпјҢжҷӢең°иҺ·жң¬пјҢзӣёдј иҮід»ҠгҖӮвҖқж…§иҝңеұ…еәҗеұұеҗҺпјҢвҖңеҲқз»ҸжөҒжұҹдёңпјҢеӨҡжңүжңӘеӨҮпјҢзҰ…жі•ж— й—»пјҢеҫӢи—Ҹж®ӢйҳҷгҖӮиҝңеӨ§еӯҳж•ҷжң¬пјҢж„Өж…ЁйҒ“зјәпјҢд№ғе‘Ҫејҹеӯҗжі•еҮҖзӯүиҝңеҜ»дј—з»ҸпјҢиё°и¶ҠжІҷйӣӘпјҢж—·иҪҪж–№иҝҳгҖӮзҡҶиҺ·ж№–жң¬пјҢеҫ—д»Ҙдј иҜ‘гҖӮжҜҸйҖўиҘҝеҹҹдёҖе®ҫпјҢиҫ„жҒіжҒ»е’Ёи®ҝгҖӮеұЎйҒЈдҪҝе…Ҙе…іпјҢиҝҺиҜ·зҰ…еёҲпјҢи§Је…¶ж‘ҲдәӢпјҢдј еҮәзҰ…з»ҸгҖӮеҸҲиҜ·зҪҪе®ҫжІҷй—Ёеғ§дјҪжҸҗе©ҶеҮәж•°з»ҸгҖӮжүҖд»ҘзҰ…жі•з»ҸжҲ’пјҢзҡҶеҮәеәҗеұұпјҢеҮ дё”зҷҫеҚ·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иҷҪ然没жңүзӣҙжҺҘи®°иҪҪж…§иҝңдәҺжӯҰжҳҢйҒҚи®ҝз»ҸеҚ·зҡ„е…·дҪ“з»ҸиҝҮеҸҠ其收иҺ·пјҢдҪҶеҸҜд»ҘзңӢеҮәеҢ…жӢ¬еұ…з•ҷжӯҰжҳҢдёӨе№ҙеӨҡзҡ„ж—¶й—ҙеңЁеҶ…пјҢж…§иҝңдәҺжҗңйӣҶдҪӣж•ҷз»ҸеҚ·ж–№йқўзҡ„й•ҝжңҹеқҡжҢҒе’Ңжҳҫи‘—жҲҗе°ұгҖӮеӣ жӯӨйҮҠеғ§дҪ‘еңЁгҖҠеҮәдёүи—Ҹи®°йӣҶВ·ж…§иҝңжі•еёҲдј гҖӢдёӯиөһеҸ№йҒ“пјҡвҖңи‘ұеӨ–еҰҷе…ёпјҢе…ідёӯиғңиҜҙпјҢжүҖд»ҘжқҘйӣҶе…№еңҹиҖ…пјҢзҡҶиҝңд№ӢеҠӣд№ҹгҖӮвҖқеҜ№ж…§иҝңй•ҝжңҹи®ҝеҜ»дҪӣж•ҷз»ҸеҚ·з»ҷдәҲдәҶеҫҲй«ҳзҡ„иҜ„д»·гҖӮ
е»әиҘҝеұұеҸӨеҜәгҖӮжҚ®жё…д»Ј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и®°иҪҪпјҢдёңжҷӢж—¶жӯҰжҳҢжЁҠеұұжңүеӨҡеә§дҪӣеҜәпјҢе…¶дёӯжҜ”иҫғи‘—еҗҚзҡ„жңүдёӨеә§гҖӮ
дёҖдёәвҖңеҜ’жәӘеҜәвҖқгҖӮе…үз»Ә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еҜ’жәӘеҜәеңЁеҺҝеҜ’жәӘдёҠпјҢдёҖеҗҚиө„еңЈеҜәгҖӮжҷӢйҷ¶дҫғи§Ғ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иҸ©иҗЁеғҸпјҢйҖҒжӯҰжҳҢеҜ’жәӘеҜәгҖӮвҖқйҷ¶дҫғз”ҹдәҺе…¬е…ғ259е№ҙпјҢеҚ’дәҺе…¬е…ғ334е№ҙпјҢеҺҶз»ҸдёүеӣҪе’ҢеүҚеҗҺдёӨжҷӢпјҢеӨҡж¬ЎеңЁжӯҰжҳҢдёәе®ҳпјҢеңЁжӯҰжҳҢең°еҢәжңүиүҜеҘҪзҡ„е®ҳеЈ°гҖӮиҘҝжҷӢеӯқж„Қеёқж—¶пјҢйҷ¶дҫғеӣ еҸ—зҺӢж•ҰжҺ’жҢӨпјҢиў«йҷҚи°ғдёәе№ҝе·һеҲәеҸІгҖӮжңүдёҖж¬Ўжё”дәәд»Һжө·йҮҢиҺ·еҫ—дёҖ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иҸ©иҗЁйҮ‘еғҸпјҢйҖҒеҲ°йҷ¶дҫғеӨ„пјҢйҷ¶дҫғе°Ҷиҝҷе°ҠдҪӣеғҸйҖҒз»ҷдәҶжӯҰжҳҢиҘҝеұұдёҠзҡ„еҜ’жәӘеҜәгҖӮеҜ’жәӘеҜәе§Ӣе»әдҪ•ж—¶пјҢд»ҠеӨ©е·ІдёҚи§Ғж–ҮзҢ®и®°иҪҪгҖӮдҪҶд»Һйҷ¶дҫғдҫӣеғҸзҡ„ж—¶й—ҙеҸҜд»ҘиӮҜе®ҡпјҢеҜ’жәӘеҜәеңЁиҘҝжҷӢдҫҝе·Із»ҸеӯҳеңЁгҖӮеҗҺжқҘйҷ¶дҫғеңЁд»»жұҹе·һеҲәеҸІжңҹй—ҙпјҢеҜ’жәӘеҜәеӨұзҒ«иў«еӨ§йғЁеҲҶзғ§жҜҒпјҢзӢ¬дҫӣеҘү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иҸ©иҗЁйҮ‘еғҸзҡ„еӨ„жүҖе®ү然еӯҳеңЁгҖӮгҖҠй«ҳеғ§дј В·жҷӢеәҗеұұйҮҠж…§иҝң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жҳ”жө”йҳійҷ¶дҫғз»Ҹй•Үе№ҝе·һпјҢжңүжё”дәәдәҺжө·дёӯи§ҒзҘһе…үпјҢжҜҸеӨ•иүіеҸ‘пјҢз»Ҹж—¬ејҘзӣӣпјҢжҖӘд»ҘзҷҪдҫғпјҢдҫғеҫҖиҜҰи§ҶпјҢд№ғжҳҜйҳҝиӮІзҺӢеғҸпјҢеҚіжҺҘеҪ’д»ҘйҖҒжӯҰжҳҢеҜ’жәӘеҜәгҖӮеҜәдё»еғ§зҸҚе°қеҫҖеӨҸеҸЈпјҢеӨңжўҰеҜәйҒӯзҒ«пјҢиҖҢжӯӨеғҸеұӢзӢ¬жңүйҫҷзҘһеӣҙйҒ¶гҖӮзҸҚи§үпјҢй©°иҝҳеҜәпјҢеҜәж—ўз„ҡе°ҪпјҢе”ҜеғҸеұӢеӯҳз„үгҖӮвҖқ
иҘҝеұұеҜәжҳҜе…үз»Ә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и®°иҪҪзҡ„жҷӢд»ЈжЁҠдёҠеҸҰдёҖеә§и‘—еҗҚдҪӣеҜәпјҡвҖңиҘҝеұұеҜәеңЁеҺҝиҘҝпјҢжҷӢе»әгҖӮжҷӢеӨӘе…ғдёӯпјҢеғ§ж…§иҝңе»әгҖӮж—§еҗҚиө„зҰҸеҜәгҖӮвҖқжҳҺгҖҠеҜ°е®ҮйҖҡеҝ—гҖӢиҪҪпјҡвҖңиҘҝеұұеҜәпјҢеңЁжӯҰжҳҢеҺҝжІ»иҘҝпјҢжҷӢеӨӘе…ғй—ҙиҝңе…¬жі•еёҲе»әпјҢеӣҪеҲқйҮҚе»әгҖӮжӯЈз»ҹе…ӯе№ҙеӨҚдҝ®гҖӮвҖқ
еӨӘе…ғжҳҜдёңжҷӢеӯқжӯҰеёқеҸёй©¬жӣңзҡ„第дәҢдёӘе№ҙеҸ·пјҢж—¶й—ҙеңЁе…¬е…ғ376--396е№ҙпјҢжӯЈжҳҜж…§иҝңеұ…з•ҷжӯҰжҳҢзҡ„ж—¶жңҹгҖӮеӨ§зәҰеңЁеҜ’жәӘеҜәзҒ«зҒҫд»ҘеҗҺ40--50е№ҙпјҢж…§иҝңзҺҮеҫ’дј—еҲ°жӯӨжҡӮдҪҸпјҢи§ҒдҫӣеҘү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иҸ©иҗЁйҮ‘еғҸзҡ„еӨ„жүҖеҺҶз»ҸзҒ«зҒҫпјҢдәҺжҳҜе…јиҫҹеҗҙзҺӢеӯҷжқғйҒҝжҡ‘е®«ж•…еҹәпјҢеңЁеҜ’жәӘд№ӢдёҠе»әиҘҝеұұеҜәгҖӮвҖңж•…е®һжңүйҷ¶еЈ«иЎҢд»ҘйҳҝиӮІзҺӢй“ё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йҮ‘еғҸйҖҒеҜ’жәӘдәӢпјҢиҝңе…¬еңЁеҜ’жәӘпјҢе…јиҫҹжӯӨеҜәпјҲиҘҝеұұеҜәпјүвҖқгҖӮеҸҜи§ҒеҪ“ж—¶ж…§иҝңж–°иҫҹиҘҝеұұеҜәпјҢжңү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зӣ®зҡ„пјҢе°ұжҳҜдҫӣеҘүж–Үж®ҠйҮ‘еғҸгҖӮ
ж…§иҝңзҰ»ејҖжӯҰжҳҢиҘҝеұұеҗҺпјҢеҗҺдё–е°Ҷеұұй—ҙеҜ’жәӘдёҠдёҖеӨ„зҹіжЎҘе‘ҪеҗҚдёәвҖңиҝңе…¬жЎҘвҖқгҖӮе…үз»Ә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и®°иҪҪпјӣвҖңж—§зҹіжЎҘеңЁеҜ’жәӘеҜәеүҚгҖӮзҹіжЎҘдёҖеұӮпјҢж°ҙе•®дёҚеқҸгҖӮжң¬еҗҚи—ӨжЎҘпјҢж—Ғжңүзў‘пјҢеҲ»иҝңе…¬жЎҘгҖӮвҖқжҳҺд»ЈиҜ—еғ§йҮҠжҲ’жҳҫжңүгҖҠеҜ’жәӘеҜәгҖӢиҜ—еҶҷйҒ“пјҡвҖңеҜ’жәӘе§ӢдҪ•ж—¶пјҢиҝңе…¬ж—§жі•зӘҹгҖӮејҖж“ҳе…Ҳдёңжһ—пјҢзӯ‘жЎҘжң«и—“жІЎгҖӮвҖқе…¶иҜ—ж„ҸеҚіеҜ’жәӘеҜәд№ғж…§иҝңи®Із»Ҹдҝ®иЎҢд№Ӣең°пјҢжҜ”еәҗеұұдёңжһ—еҜәпјҢејҖиҫҹиҰҒж—©еҫ—еӨҡгҖӮ
иҜ·ж–Үж®ҠйҮ‘еғҸгҖӮж…§иҝңеҲқеҲ°жӯҰжҳҢеұ…еҜ’жәӘеҜәпјҢи§Ғ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иҸ©иҗЁйҮ‘еғҸдҫӣеҘүдәҺзҒ«зҒҫеҗҺе№ҙд№…еӨұдҝ®зҡ„ж®Ӣз ҙеҜәеәҷпјҢеҚіиҫҹеҗҙзҺӢйҒҝжҡ‘е®«ж•…еҹәж–°е»әиҘҝеұұеҜәпјҢе»әжҲҗеҗҺе°ҶйҮ‘еғҸиҝҺиҜ·еҲ°еҜәеҶ…дҫӣеҘүгҖӮе…¬е…ғ381е№ҙж…§иҝңеҫ—еәҗеұұдёңжһ—еҜәпјҢеҶҚеӣһиҘҝеұұиҝҺиҜ·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иҸ©иҗЁйҮ‘еғҸгҖӮ
жӯҰжҳҢеҜ’жәӘеҜәдёҺ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иҸ©иҗЁйҮ‘еғҸ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ҢжҳҜдј—еӨҡж–ҮзҢ®е…ёзұҚи®°иҪҪзҡ„дёҖж®өдҪіиҜқгҖӮжҳҜжӯҰжҳҢеҜ’жәӘеҜәгҖҒиҘҝеұұеҜәдёҺеәҗеұұдёңжһ—еҜәд№Ӣй—ҙзү№ж®ҠиҒ”зі»зҡ„еҺҶеҸІи§ҒиҜҒгҖӮгҖҠй«ҳеғ§дј В·жҷӢеәҗеұұйҮҠж…§иҝң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дҫғеҗҺ移й•ҮпјҢд»ҘеғҸжңүеЁҒзҒөпјҢйҒЈдҪҝиҝҺжҺҘгҖӮж•°еҚҒдәәдёҫд№ӢиҮіж°ҙпјҢеҸҠдёҠиҲ№пјҢиҲ№еҸҲиҰҶжІЎпјҢдҪҝиҖ…жғ§иҖҢеҸҚд№ӢпјҢз«ҹдёҚиғҪиҺ·гҖӮдҫғе№јеҮәйӣ„жӯҰпјҢзҙ и–„дҝЎжғ…пјҢж•…иҚҶжҘҡд№Ӣй—ҙдёәд№Ӣи°Јжӣ°пјҡйҷ¶жғҹеү‘йӣ„пјҢеғҸд»ҘзҘһж ҮгҖӮдә‘зҝ”жіҘе®ҝпјҢйӮҲдҪ•йҒҘйҒҘ?еҸҜд»ҘиҜҡиҮҙпјҢйҡҫд»ҘеҠӣжӢӣгҖӮеҸҠиҝңеҲӣеҜәж—ўжҲҗпјҢзҘҲеҝғеҘүиҜ·пјҢд№ғйЈҳ然иҮӘиҪ»пјҢеҫҖиҝҳж— жў—гҖӮж–№зҹҘиҝңд№ӢзҘһж„ҹпјҢиҜҒеңЁйЈҺи¬ЎзҹЈгҖӮвҖқиҝҷдёӘиҝҮзЁӢе®ӢзүҲгҖҠзўӣз ӮеӨ§и—Ҹз»ҸгҖӢзҡ„и®°иҪҪдёҺгҖҠй«ҳеғ§еӮіВ·жҷӢеәҗеұұйҮҠж…§иҝңгҖӢзҡ„и®°иҪҪеҹәжң¬дёҖиҮҙпјҡвҖңжҷӢйҷ¶дҫғй•Үе№ҝе·һж—¶пјҢжңүжё”дәәеӨңй—ҙеҸ‘зҺ°жө·дёӯзҘһе…үж¶Ңиө·пјҢж—¬ж—ҘдёҚж•ЈпјҢжҠҘдәҺдҫғе‘ҪдәәжҚһеҸ–пјҢеҫ—еҚ°еәҰйҳҝиӮІзҺӢй“ёйҖ зҡ„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йҮ‘еғҸпјҢйҖҒеҲ°жӯҰжҳҢеҜ’жәӘеҜәдҫӣеҘүгҖӮеҗҺжқҘйҷ¶дҫғи°ғд»»жұҹе·һеҲәеҸІпјҢй—»еҜ’жәӘеҜәеӨұзҒ«пјҢзӢ¬дҫӣеҘүж–Үж®ҠеёҲеҲ©иҸ©иҗЁзҡ„еӨ„жүҖе®ү然еӯҳеңЁпјҢйҒӮжҙҫдәәз”ЁиҲ№иҝҺиҜ·йҮ‘еғҸеҫҖжұҹе·һ;дёҚж–ҷеңЁйҮ‘еғҸдёҠиҲ№еүҚдёҖеҲ»пјҢиҲ№еҝҪиў«еӨ§йЈҺиҰҶжІЎпјҢеӣ иҖҢдёӯжӯўгҖӮеҪ“ж—¶жӯҰжҳҢең°еҢәжңүж°‘и°Јдј жӣ°пјҡйҷ¶жғҹеү‘жӨҺпјҢеғҸд»ҘзҘһж ҮгҖӮдә‘зҝ”жіҘе®ҝпјҢйӮҲдҪ•йҒҘйҒҘгҖӮеҸҜд»ҘиҜҡиҮҙпјҢйҡҫд»ҘеҠӣжӢӣгҖӮвҖқеӨ§еёҲжҢүз…§ж°‘и°Јзҡ„иҜҙжі•иҷ”иҜҡзҘ·д№ӢпјҢйЎәеҲ©ең°иҝҺйҮ‘еғҸиҮіеәҗеұұдёңжһ—еҜәзҘһиҝҗж®ҝпјҢйҖ йҮҚйҳҒд»ҘдҫӣеҘүпјҢ并еҲ¶ж–Үж®Ҡз‘һеғҸиөһгҖӮ
йҷ¶дҫғеҲқйҖҒжӯҰжҳҢеҜ’жәӘеҜәж–Үж®ҠйҮ‘еғҸпјҢеңЁдёӯеӣҪдҪӣж•ҷдј ж’ӯиҝҮзЁӢдёӯе…·жңүйқһеёёзү№еҲ«зҡ„иұЎеҫҒжҖ§ең°дҪҚпјҢеңЁдёӯеӣҪдҪӣж•ҷеҜәеәҷеҸҠе…¶еғ§дј—дёӯе…·жңүжһҒе…¶зү№ж®Ҡзҡ„еҪұе“ҚеҠӣгҖӮгҖҠе”җй«ҳеғ§дј 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еҚ—жңқйҷҲжң«пјҢй«ҳеғ§йҮҠжҷәеҮҜвҖңзӯ–жқ–иҚҶж№ҳпјҢи·Ҝж¬ЎзӣҠеҹҺпјҢжўҰиҖҒеғ§жӣ°пјҡ"йҷ¶дҫғз‘һеғҸ敬еұҲжҠӨжҢҒгҖӮвҖқдәҺеҚіеҫҖжҶ©еҢЎеұұпјҢи§ҒиҝңеӣҫзјӢпјҢйӘҢе…¶зҒөд№ҹпјҢе®ӣеҰӮе…¶жўҰгҖӮдёҚд№…жө”йҳіеҸҚеҸӣеҜәе®Үз„ҡзғ§пјҢзӢ¬еңЁе…№еұұе…Ёж— дҫөжү°пјҢдҝЎжҠӨеғҸд№ӢеҠӣзҹЈгҖӮвҖқиҝҷдёӘж•…дәӢи®°иҝ°зҡ„жҳҜпјҢеҚ—жңқйҷҲеҖҫиҰҶд№Ӣйҷ…пјҢй«ҳеғ§йҮҠжҷәеҮҜеҲ°иҚҶ(ж№–еҢ—)гҖҒж№ҳ(ж№–еҚ—)дёҖеёҰжёёеҢ–ејҳжі•гҖӮи·ҜиҝҮзӣҠеҹҺж—¶пјҢжўҰи§ҒдёҖдёӘиҖҒеғ§еҜ№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иҝҮеҺ»йҷ¶дҫғе®ҲжҠӨд№Ӣз‘һеғҸзҺ°еңЁеәҗеұұпјҢиҜ·дҪ иғҪеҲ°йӮЈйҮҢеҺ»з»§з»ӯжҠӨжҢҒгҖӮвҖқдәҺжҳҜд»–е°ұдҫқйӮЈиҖҒеғ§д№ӢиЁҖеҲ°дәҶеәҗеұұпјҢзңӢеҲ°дәҶеӣҫеғҸпјҢе®ӣеҰӮжўҰдёӯжүҖиҜҙпјҢиҜҒжҳҺиҖҒеғ§д№ӢиҜӯдёҚиҷҡгҖӮиҝҮдәҶдёҚд№…пјҢд№қжұҹдёҖеёҰеҸ‘з”ҹе…өд№ұпјҢи®ёеӨҡеҜәйҷўйғҪиў«зғ§жҜҒпјҢзӢ¬еәҗеұұд№ӢеҜәйҷўе®ҢеҘҪж— жҚҹпјҢз¬ғдҝЎиҝҷжҳҜеӣ дёәжҠӨеғҸд№ӢеҠҹеҫ·жүҖиҮҙгҖӮ
вҖңдјҡжҳҢжҜҒеҜәпјҢдәҢеғ§иҙҹж–Үж®ҠеғҸпјҢи—Ҹд№Ӣй”Ұз»Ји°·д№Ӣеі°йЎ¶гҖӮиҮіжҳҜеҜәеӨҚпјҢи®ҝд№ӢдёҚиҺ·пјҢдәҢеғ§зӣёз–‘пјҢд»ҘдёәеҢҝеҺ»пјҢеҝҪи§ҒеңҶе…үз‘һзӣёж¶ҢдәҺз©әиЎЁпјҢиҮӘжҳҜеі°йЎ¶дҪӣжүӢеІ©еӨ©жұ еёёи§Ғе…үзӣёгҖӮвҖқиҝҷжҳҜгҖҠдҪӣзҘ–з»ҹи®°гҖӢе…ідәҺж–Үж®ҠйҮ‘еғҸе…Ҙдёңжһ—еҜәзҡ„еҗҺи®°гҖӮе…үз»Ә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д№ҹиҪҪпјҡвҖңж…§иҝңиҝҺеҪ’еәҗеұұпјҢеұұдёӯдё–д»ҘдәҢеғ§е®Ҳд№ӢпјҢдјҡжҳҢиҜҸжҜҒдҪӣеҜәпјҢдәҢеғ§и—ҸеғҸй”Ұз»Ји°·дёӯгҖӮжҜ”йҮҠж•ҷеӨҚе…ҙпјҢжұӮеғҸдёҚеҸҜеҫ—гҖӮвҖқ
пјҲ3пјүвҖңеҮҖеңҹе®—вҖқеҲқзҘ–
дёӨжҷӢж—¶жңҹпјҢжӯҰжҳҢжЁҠеұұпјҲиҘҝеұұпјүе·ІжҳҜйҒҗиҝ©й—»еҗҚзҡ„дҪӣж•ҷеҗҚеұұгҖӮиҝҷйҮҢдёҚд»…дҝқз•ҷзқҖдј—еӨҡдёүеӣҪеҺҶеҸІж–ҮеҢ–йҒ—еӯҳпјҢд№ҹеӯҳеңЁеӨҡеӨ„дҪӣж•ҷжҙ»еҠЁеңәжүҖгҖӮдёүеӣҪж—¶жңҹдҝ®е»әзҡ„ж…§е®қеҜәдёҺе®қе®ҒйҷўеңЁжЁҠеұұдёңйә“пјҢжҷӢеҲқдҫҝе·ІеӯҳеңЁзҡ„еҜ’жәӘеҜәеңЁеұұдёӢжәӘиҫ№гҖӮжҷӢеӨӘе…ғй—ҙпјҢж…§иҝңе…јиҫҹеҗҙзҺӢйҒҝжҡ‘е®«ж–°е»әиҘҝеұұеҜәпјҢ并еңЁжӯӨејҳжі•дҝ®иЎҢпјҢеҫ’еұһж—Ҙдј—пјҢ并且慕еҗҚжқҘжҠ•й—ЁдёӢзҡ„и¶ҠжқҘи¶ҠеӨҡгҖӮиҝҷдёҖеұҖйқўеңЁж…§иҝңеҲқи®ҝеәҗеұұж—¶пјҢе…¶еёҲејҹж…§ж°ёдёҺжұҹе·һеҲәеҸІжЎ“дјҠзҡ„дёҖж®өеҜ№иҜқйҮҢиЎЁиҝ°еҫ—йқһеёёжё…жҘҡгҖӮж…§иҝңз•ҷеұ…жӯҰжҳҢжңҹй—ҙпјҢжӮүзҹҘеёҲејҹж…§ж°ёеңЁеәҗеұұеёғж•ҷдҫҝеүҚеҫҖдјҡи§ҒгҖӮж…§ж°ёдёҚеӨұж—¶жңәең°е»әи®®ж…§иҝңд№ҹеңЁеәҗеұұз•ҷдҪҸпјҢ并жүҫжұҹе·һеҲәеҸІжЎ“дјҠе•Ҷи®®пјҡвҖңиҝңе…¬ж–№еҪ“ејҳйҒ“пјҢд»Ҡеҫ’еұһе·Іе№ҝпјҢиҖҢжқҘиҖ…ж–№еӨҡгҖӮиҙ«йҒ“жүҖж –иӨҠзӢӯпјҢдёҚи¶ізӣёеӨ„пјҢеҰӮдҪ•пјҹвҖқж…§иҝңеңЁжӯҰжҳҢиҘҝеұұж—¶вҖңеҫ’еұһе·Іе№ҝпјҢиҖҢжқҘиҖ…ж–№еӨҡвҖқпјҢиӢҘеҺ»еәҗеұұпјҢж…§ж°ёжүҖеұ…зҡ„иҘҝжһ—еҜәвҖңжүҖж –иӨҠзӢӯпјҢдёҚи¶ізӣёеӨ„вҖқпјҢжЎ“дјҠдәҺжҳҜеңЁеәҗеұұзҡ„дёңйқўдё“дёәж…§иҝңе»әйҖ жҲҝж®ҝпјҢе°ұжҳҜеҗҺжқҘи‘—еҗҚзҡ„дёңжһ—еҜәгҖӮ
ж…§иҝңй•ҝжңҹеқҡжҢҒд»ҘгҖҠйҳҝејҘйҷҖгҖӢгҖҠи§Ӯж— йҮҸеҜҝгҖӢзӯүдҪӣз»ҸдёәеҮҶеҲҷпјҢеҖЎеҜјз§°еҝөдҪӣеҸ·зҡ„вҖңеҚ—ж— йҳҝејҘйҷҖдҪӣвҖқпјҢзҘҲжұӮеҫҖз”ҹиҘҝж–№жһҒд№җдё–з•ҢгҖӮеңЁжӯҰжҳҢиҘҝеұұй©»й”ЎдёӨе№ҙпјҢжҪңдҝ®еҮҖеңҹпјҢеҫ’дј—ж—ҘеӨҡгҖӮеҫ—еәҗеұұдёңжһ—еҜәеҗҺпјҢиҮӘжӯӨд»Ҙдёңжһ—дёәйҒ“еңәпјҢдҝ®иә«ејҳйҒ“пјҢи‘—д№Ұз«ӢиҜҙпјҢз»“зҷҪиҺІзӨҫдәҺеұұдёӯпјҢеҪўжҲҗеҮҖеңҹе®—е®Ңж•ҙзҡ„зҗҶи®әдҪ“зі»пјҢиў«е…¬и®ӨдёәдҪӣж•ҷеҮҖеңҹе®—еҲқзҘ–гҖӮ
дҪӣж•ҷиҝӣе…ҘдёӯеӣҪпјҢе…ҲеҗҺеҪўжҲҗе…«еӨ§е®—жҙҫпјҢдёҖжҳҜдёүи®әе®—еҸҲеҗҚжі•жҖ§е®—пјҢдәҢжҳҜз‘ңдјҪе®—еҸҲеҗҚжі•зӣёе®—гҖҒж…ҲжҒ©е®—гҖҒе”ҜиҜҶе®—пјҢдёүжҳҜеӨ©еҸ°е®—еҸҲеҗҚжі•еҚҺе®—пјҢеӣӣжҳҜиҙӨйҰ–е®—еҸҲеҗҚеҚҺдёҘе®—пјҢдә”жҳҜзҰ…е®—пјҢе…ӯжҳҜеҮҖеңҹе®—пјҢдёғжҳҜеҫӢе®—пјҢе…«жҳҜеҜҶе®—еҸҲеҗҚзңҹиЁҖе®—гҖӮеҚіжҖ§гҖҒзӣёгҖҒеҸ°гҖҒиҙӨгҖҒзҰ…гҖҒеҮҖгҖҒеҫӢгҖҒеҜҶе…«еӨ§е®—жҙҫгҖӮе”җд»Јд»ҘеҗҺпјҢе…¶д»–е…ӯе®—ж—ҘжёҗејҸеҫ®пјҢзҰ…е®—е’ҢеҮҖеңҹе®—еҲҷеңЁж°‘й—ҙе№ҝдёәжөҒдј пјҢдёҚиҝҮе®—жҙҫзҡ„з•Ңйҷҗи¶ҠжқҘи¶ҠжЁЎзіҠгҖӮ
дёҺе…¶д»–е®—жҙҫе«Ўдј еёҲжүҝдёҚдёҖж ·зҡ„жҳҜпјҢеҮҖеңҹе®—еҗ„зҘ–йғҪдёәеҮҖдёҡеҗҺдәәжҺЁдёҫгҖӮе®Ӣе…ғеҮҖеңҹз«Ӣе®—пјҢеҮҖдёҡеҗҺдәәеҘүж…§иҝңдёәеҲқзҘ–пјҢе®һеңЁжҳҜеҜ№еӨ§еёҲй•ҝжңҹеҝ—еҝғдәҺеҮҖеңҹзҡ„жҷ®йҒҚе…¬и®Өе’ҢдёҖиҮҙиӮҜе®ҡгҖӮеҜ№ж…§иҝңеӨ§еёҲиҖҢиЁҖпјҢеҮҖеңҹе®—еҲқзҘ–зҡ„зЎ®жҳҜе®һиҮіеҗҚеҪ’гҖӮеҚ—жҖҖз‘ҫе…Ҳз”ҹз§°пјҡвҖңж…§иҝңеӨ§еёҲеҮҖеңҹе®—зҡ„е»әз«ӢпјҢеҸҜд»ҘиҜҙжҳҜеҪўжҲҗдёӯеӣҪдҪӣж•ҷзҡ„зңҹжӯЈејҖе§ӢпјҢд№ҹжҳҜдҪӣж•ҷеҜҢжңүе®—ж•ҷзІҫзҘһжңҖжҳҺжҳҫзҡ„дёҖйқўгҖӮвҖқдёңжҷӢд»ҘжқҘпјҢеәҗеұұдёңжһ—еҜәжҲҗдёәдёӯеӣҪдҪӣж•ҷеҮҖеңҹе®—зҡ„еҸ‘жәҗең°д№ӢдёҖпјҢдёҖеәҰжҳҜдёӯеӣҪеҚ—ж–№дҪӣж•ҷзҡ„дёӯеҝғпјҢдёҺж…§иҝңеӨ§еёҲе·ЁеӨ§зҡ„еҪұе“ҚеҠӣзӣҙжҺҘзӣёе…ігҖӮдёҚиҝҮд»Һжҹҗз§Қж„Ҹд№үдёҠиҜҙпјҢе…¬е…ғ379иҮі381е№ҙпјҢж…§иҝңеӨ§еёҲеңЁжӯҰжҳҢиҘҝеұұдҝ®иЎҢпјҢдәҺеҲӣз«ӢвҖңдёүж №жҷ®иў«пјҢеҲ©й’қзҫӨ收вҖқзҡ„дҪӣж•ҷеҮҖеңҹе®—еҗҢж ·еҚҒеҲҶе…ій”®гҖӮеҫҲеӨҡж–ҮзҢ®и®°иҪҪдҪӣж•ҷеҮҖеңҹе®—еҸ‘жәҗдәҺиҘҝеұұпјҢеҪўжҲҗдәҺеәҗеұұпјҢе®һдёҚдёәиҝҮгҖӮ
ж…§иҝңиҘҝеұұдҝ®иЎҢпјҢејҳжі•еёғж•ҷпјҢдҪҝиҘҝеұұеҜәгҖҒеҜ’жәӘеҜәжҲҗдёәеҚғеҸӨеҗҚеҲ№пјҢеҺҶд»ЈйҰҷзҒ«йјҺзӣӣ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д№ҹдёәдҪӣж•ҷз»Ҹ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еҗ‘жұҹеҚ—зҡ„дј ж’ӯпјҢз•ҷдёӢдәҶжө“еўЁйҮҚеҪ©зҡ„дёҖ笔гҖӮ
3гҖҒйҡӢеҲқжӯҰжҳҢвҖңеӨ©дёӢ第дәҢеЎ”вҖқ
дҪӣж•ҷдј е…ҘдёӯеӣҪд№ӢеҲқпјҢзӨҫдјҡеҪұе“ҚеҠӣиҝҳжҜ”иҫғжңүйҷҗгҖӮдҪҶеҲ°дәҶд№ұдёҚжӯўзҡ„дёӨжҷӢеҚ—еҢ—жңқж—¶жңҹпјҢдҪӣж•ҷзҡ„вҖңиҪ®еӣһиҪ¬дё–вҖқгҖҒвҖңеӣ жһңжҠҘеә”вҖқгҖҒвҖңдј—з”ҹе№ізӯүвҖқзҗҶеҝөпјҢеёҰз»ҷжҲҳд№ұд№Ӣдёӯе‘ҪеҰӮиҚүиҠҘзҡ„жҷ®йҖҡж°‘дј—жһҒеӨ§зҡ„зІҫзҘһж…°и—үпјҢеӣ иҖҢеҫ—еҲ°иҝ…йҖҹдј ж’ӯгҖӮеҚ—еҢ—жңқж—¶жңҹпјҢ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дҫқ然жҳҜжұҹеҚ—дҪӣж•ҷйҮҚй•ҮпјҢжЁҠеұұд»Қ然жҳҜеЈ°еҗҚиҝңж’ӯзҡ„жұҹеҚ—дҪӣж•ҷеҗҚеұұгҖӮ
еҚ—жңқйҪҗж—¶пјҢжқҘжӯҰжҳҢжЁҠеұұдҝ®иЎҢзҡ„йҮҠжі•жӮҹеҸҠйҒ“жөҺпјҢжҳҜдҪӣж•ҷдҝ®д№ зҰ…е®ҡзҡ„д»ЈиЎЁжҖ§дәәзү©гҖӮ
гҖҠй«ҳеғ§еҚ·В·йҪҗжӯҰжҳҢжЁҠеұұйҮҠжі•жӮҹ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йҮҠжі•жӮҹпјҢйҪҗдәәгҖӮ家д»Ҙз”°жЎ‘дёәдёҡпјҢжңүз”·е…ӯдәәпјҢ并зҡҶжҲҗй•ҝгҖӮжӮҹе№ҙдә”еҚҒдё§еҰ»пјҢдёҫ家йғҒ然慕йҒ“пјҢзҲ¶еӯҗдёғдәәпјҢжӮүе…ұеҮә家гҖӮеҚ—иҮіжӯҰжҳҢпјҢеұҘиЎҢеұұж°ҙпјҢи§ҒжЁҠеұұд№ӢйҳіеҸҜдёәе№Ҫж –д№ӢеӨ„пјҢжң¬йҡҗеЈ«йғӯй•ҝзҝ”жүҖжӯўпјҢдәҺжҳҜжңүж„Ҹз»Ҳз„үгҖӮж—¶жӯҰжҳҢеӨӘе®ҲйҷҲз•ҷйҳ®жҷҰй—»иҖҢеҘҮд№ӢпјҢеӣ дёәеүӘеҫ„ејҖеұұпјҢйҖ з«ӢжҲҝе®ӨгҖӮжӮҹдёҚйЈҹзІізұіпјҢеёёиө„йәҰйҘӯпјҢж—ҘдёҖйЈҹиҖҢе·ІгҖӮиҜөеӨ§е°ҸгҖҠе“ҒгҖӢгҖҠжі•еҚҺгҖӢгҖӮеёёе…ӯж—¶иЎҢйҒ“пјҢеӨҙйҷҖеұұжіҪпјҢдёҚйҒҝиҷҺе…•гҖӮжңүж—¶еңЁж ‘дёӢеқҗзҰ…пјҢжҲ–з»Ҹж—ҘдёҚиө·гҖӮд»ҘйҪҗж°ёжҳҺдёғе№ҙеҚ’дәҺеұұдёӯпјҢжҳҘз§ӢдёғеҚҒжңүд№қгҖӮ еҗҺжңүжІҷй—ЁйҒ“жөҺпјҢиёөе…¶й«ҳдёҡгҖӮд»ҠжӯҰжҳҢи°“е…¶жүҖдҪҸдёәеӨҙйҷҖеҜәз„үгҖӮвҖқ
йҮҠжі•жӮҹ家ж—Ҹд»ҘеҶңдёҡе’Ңз§ҚжӨҚжЎ‘ж ‘дёәдёҡгҖӮд»–жңүе…ӯдёӘе„ҝеӯҗпјҢе…ЁйғҪжҲҗй•ҝжҲҗдәәгҖӮеңЁд»–дә”еҚҒеІҒж—¶еҰ»еӯҗеҺ»дё–пјҢж•ҙдёӘ家еәӯйғҪеҫҲеҝ§йғҒ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зҲ¶еӯҗдёғдәәдёҖиө·иҲҚдҝ—еҮә家пјҢеҲ°жӯҰжҳҢжЁҠеұұеҚ—еқЎжүҫеҲ°дёҖдёӘе№Ҫйқҷ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еҶіе®ҡеңЁиҝҷйҮҢз»ҲиҖҒгҖӮ
еҪ“ж—¶пјҢжӯҰжҳҢеӨӘе®Ҳйҳ®жҷҰеҗ¬й—»д»–们зҡ„дәӢиҝ№еҗҺйқһеёёжғҠеҘҮпјҢдәҺжҳҜдёә他们ејҖиҫҹеұұи·ҜпјҢе»әйҖ жҲҝеұӢгҖӮжі•жӮҹдёҚеҗғзІізұіпјҢеёёеҗғйәҰйҘӯпјҢжҜҸеӨ©еҸӘеҗғдёҖйЎҝгҖӮд»–еёёеёёиҜөиҜ»еӨ§е°Ҹе“ҒгҖҒгҖҠжі•еҚҺз»ҸгҖӢпјҢжҜҸж—¶жҜҸеҲ»йғҪеңЁдҝ®иЎҢпјҢеңЁеұұжһ—дёӯиЎҢеӨҙйҷҖд№ӢйҒ“пјҢдёҚйҒҝејҖзҢӣе…ҪгҖӮжңүж—¶еңЁж ‘дёӢжү“еқҗдҝ®иЎҢпјҢз”ҡиҮідёҖж•ҙеӨ©дёҚиө·еқҗгҖӮд»–еңЁйҪҗж°ёжҳҺдёғе№ҙеҚіе…¬е…ғ489е№ҙеңҶеҜӮдәҺеұұдёӯпјҢдә«е№ҙдёғеҚҒд№қеІҒгҖӮеҗҺжқҘжңүдёҖдёӘжІҷй—ЁйҒ“жөҺпјҢ继жүҝдәҶд»–зҡ„иЎЈй’өпјҢд»–й©»й”Ўзҡ„еҜәйҷўиў«з§°дёәеӨҙйҷҖеҜәгҖӮдј дёӯжҸҗеҲ°еӨҙйҷҖеҜәеҹәжӣҫз»ҸжҳҜжҷӢд»ЈйҡҗеЈ«йғӯй•ҝзҝ”еңЁжӯҰжҳҢзҡ„йҡҗеұ…д№ӢжүҖпјҢдҪҚдәҺжЁҠеұұеҚ—еқЎзҡ„еҜҶжһ—д№ӢдёӯпјҢеҗҺдёәеҪ“ж—¶жӯҰжҳҢеӨӘе®Ҳйҳ®жҷҰиө„е»әгҖӮйғӯй•ҝзҝ”жҳҜжҷӢд»ЈжӯҰжҳҢеҗҚдәәпјҢгҖҠжҷӢд№Ұ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йғӯзҝ»пјҢеӯ—й•ҝзҝ”пјҢжӯҰжҳҢдәәд№ҹгҖӮдјҜзҲ¶и®·пјҢе№ҝе·һеҲәеҸІгҖӮзҲ¶еҜҹпјҢе®үеҹҺеӨӘе®ҲгҖӮзҝ»е°‘жңүеҝ—ж“ҚпјҢиҫһе·һйғЎиҫҹеҸҠиҙӨиүҜд№ӢдёҫгҖӮ----дёәеәҫдә®жүҖиҚҗпјҢе…¬иҪҰеҚҡеЈ«еҫҒпјҢдёҚе°ұгҖӮвҖқеӨҙйҷҖеҜәеңЁжҳҺжё…жӯҰжҳҢең°ж–№еҸІеҝ—дёӯдёҚи§Ғи®°иҪҪгҖӮдҪҶгҖҠеәҗеұұи®°гҖӢеҚ·дә”收еҪ•зҡ„гҖҠдёңжһ—еҜәиҝңжі•еёҲеҪұе Ӯзў‘(并еәҸ)гҖӢдёӯпјҢжңүвҖңйҷҮиҘҝжқҺжј”иҝ°пјҢжұҹе·һеҪ•дәӢеҸӮеҶӣзҺӢйҖҡзҜҶйўқпјҢй„Ӯе·һеӨҙйҷҖеҜәеғ§жғҹеө©д№ҰгҖӮиҙһе…ғдёӯеҲқе»әпјҢеӨ§дёӯе…«е№ҙдёғжңҲеҚҒдә”ж—ҘеҶҚз«ӢвҖқзҡ„и®°иҝ°гҖӮе”җиҙһе…ғе№ҙеҸ·еңЁе…¬е…ғ785-805е№ҙй—ҙпјҢиҜҙжҳҺй„Ӯе·һеӨҙйҷҖеҜәеңЁе”җд»ЈдёӯеҗҺжңҹд»Қ然еӯҳеңЁгҖӮ
еҚ—жңқжўҒж—¶пјҢжҳӯжҳҺеӨӘеӯҗиҗ§з»ҹиӢұе№ҙж—©йҖқпјҢе…¶еӯҗиҗ§ж••дәҺеӨ§еҗҢдёүе№ҙпјҲ537е№ҙпјүе°ҒдёәжӯҰжҳҢйғЎзҺӢгҖӮдёәи¶…еәҰе…¶зҲ¶пјҢдәҺеӨ§еҗҢе…ӯе№ҙпјҲе…¬е…ғ540е№ҙпјүдҝ®е»әеҚҺе®№еҜәгҖӮе…¶еҸ”зҲ¶жӯҰйҷөзҺӢиҗ§зәӘдёәд№Ӣж’°гҖҠеҚҺе®№еҜәзў‘гҖӢгҖӮе”җиҙһи§Ӯе№ҙй—ҙпјҢй«ҳеғ§жғ е…үдҝ®зҰ…жӯӨеҜәгҖӮжҚ®еҚ—е®ӢгҖҠиҲҶең°зәӘиғң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еғ§жғ е…үпјҢжӯҰжҳҢи®°дә‘пјҢеҺҝиҘҝдә”еҚҒйҮҢжңүеҚҺе®№еҜәпјҢж—§еҗҚзҰ…жһ—еҜәгҖӮе”җжӯЈи§ӮдёӯеәөеүҚжңүдёҖж ‘пјҢж ‘дёҠжңүи—ӨпјҢжҜҸи§ҒдёҖз—…йј ж— жҜӣпјҢжІҝж ‘иҖҢйЈҹеҚҠжңҲдҪҷжҜӣз”ҹпјҢеҪ“ж—¶ж–ҮзҡҮеңЈдҪ“дёҚеә·пјҢжғ е…үйҮҮе…¶и—Өд»ҘиҝӣпјҢжӣ°зҷҫзҒөи—ӨпјҢеёқжңҚд№Ӣз–ҫж„ҲгҖӮжғ е…үжұӮеҪ’еҫЎжңӯпјҢе»әеҜәд»ҘеӨ„пјҢжӣ°зҰ…жһ—гҖӮвҖқејҖе…ғдәҢеҚҒдә”е№ҙпјҲе…¬е…ғ737е№ҙпјүиҜҘеҜәйҮҚдҝ®пјҢж”№вҖңзҰ…жһ—вҖқдёәвҖңеҚҺе®№вҖқгҖӮйҮҚдҝ®ж—¶ж®ҝдёӯжңүзҹіеҲ»ж—§з»ҸеҸҠжўҒжӯҰйҷөзҺӢгҖҠеҚҺе®№еҜәзў‘гҖӢгҖӮвҖқ
еҚ—жңқжўҒж—¶пјҢйӮөйҷөзҺӢиҗ§дјҰеңЁжЁҠеұұе»әж— зӣёеҜәгҖӮжҚ®дј пјҢжўҒз®Җж–ҮеёқеӨ§е®қе…ғе№ҙпјҲе…¬е…ғ550е№ҙпјүдәҢжңҲпјҢдҫҜжҷҜйҒЈд»»зәҰгҖҒдәҺеәҶзӯүеё…дәҢдёҮдҪҷдј—ж”»иҜёи—©гҖӮз§Ӣе…«жңҲпјҢйӮөйҷөзҺӢиҗ§дјҰеӨ§дҝ®еҷЁз”ІпјҢе°Ҷи®ЁдҫҜжҷҜгҖӮе…ғеёқй—»е…¶ејәзӣӣпјҢд№ғйҒЈзҺӢеғ§иҫ©её…иҲҹеёҲеҚҒдёҮпјҢд»ҘйҖјдјҰгҖӮдјҰеҶӣжәғпјҢйҒӮдёҺеӯҗзўәзӯүиҪ»иҲҹиө°жӯҰжҳҢгҖӮ涧йҘ®еҜәеғ§жі•йҰЁдёҺдјҰжңүж—§пјҢи—Ҹд№ӢдәҺеІ©зҹід№ӢдёӢгҖӮеҗҺйӮөйҷөзҺӢдёәжҠҘзӯ”еҜәеғ§пјҢдҝ®ж— зӣёеҜәгҖӮе…үз»Ә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иҪҪпјҡвҖңж— зӣёеҜәеңЁеҺҝиҘҝжЁҠеұұй—ҙпјҢдёүйқўйҳ»еҚұеі°гҖӮж—§з»Ҹдә‘пјҡжўҒеӨ§еҗҢй—ҙпјҢйӮөйҷөзҺӢиҗ§зә¶е»әгҖӮж°ёжҳҺеӣӣе№ҙпјҢд№җе№ізҺӢ移еҜәдәҺ涧йҘ®еҜәеҹәдёҠпјҢдёәд№җе№іеҜәгҖӮе®ӢеӨ§дёӯзҘҘз¬Ұе…ғе№ҙпјҢж”№еҗҚвҖҳж— зӣёвҖҷвҖқгҖӮ
еҸӨиҜӯжңүдә‘пјҢеұұдёҚеңЁй«ҳпјҢжңүд»ҷеҲҷеҗҚгҖӮ收еҪ•еңЁеҚ—жңқжўҒд»ЈйҮҠж…§зҡҺжүҖж’°гҖҠй«ҳеғ§дј гҖӢдёӯзҡ„пјҢйғҪжҳҜдҪӣж•ҷдј е…ҘдёӯеӣҪд»ҘеҗҺпјҢеҲ°еҚ—жңқжўҒд»ЈеӨ©зӣ‘еҚҒе…«е№ҙиҝҷж•°зҷҫе№ҙй—ҙпјҢеңЁдҪӣз»Ҹзҝ»иҜ‘гҖҒд№үзҗҶйҳҗйҮҠгҖҒејҳжі•е®һи·өдёӯжңүзӘҒеҮәжҲҗе°ұжҲ–зү№ејӮиЎЁзҺ°иҖ…пјҢдј дё»й«ҳеғ§е…ұжңү257дәәгҖӮе…¶дёӯж”Ҝи°Ұе’Ңз»ҙзҘҮйҡҫд»ҘеҸҠз«әеҫӢзӮҺеңЁдҪӣз»Ҹзҝ»иҜ‘гҖҒж…§иҝңеңЁд№үзҗҶйҳҗйҮҠгҖҒйҮҠжі•жӮҹеңЁдҝ®д№ зҰ…е®ҡж–№йқўйғҪжҳҜд»ЈиЎЁжҖ§дәәзү©пјҢиҝҷдәӣдј дё»й«ҳеғ§йғҪжӣҫз•ҷй©»дҝ®иЎҢдәҺжӯҰжҳҢжЁҠеұұпјҢи¶іи§ҒжЁҠеұұеңЁжұҹеҚ—ж—©жңҹдҪӣж•ҷдј ж’ӯиҝҮзЁӢдёӯзҡ„еҺҶеҸІең°дҪҚгҖӮ
йҡӢжңқз»ҹдёҖдёӯеӣҪд»ҘеҗҺпјҢдҪӣж•ҷзҡ„ең°дҪҚиҫҫеҲ°йјҺзӣӣгҖӮйҡӢж–ҮеёқжқЁеқҡдәҺејҖзҡҮ20е№ҙж”№е…ғд»ҒеҜҝгҖӮд»ҒеҜҝе…ғе№ҙпјҲе…¬е…ғ601е№ҙпјүе…ӯжңҲпјҢжқЁеқҡеҗҢж—¶еҒҡдәҶеҮ 件зҹіз ҙеӨ©жғҠзҡ„еӨ§дәӢпјҢдёҖжҳҜжҙҫйҒЈеҚҒе…ӯдҪҝеҲ°еҗ„ең°е·ЎзңҒйЈҺдҝ—пјҢи®ҝжҹҘең°ж–№е®ҳжІ»з»©пјӣдәҢжҳҜе®ЈеёғеәҹйҷӨдёӯеӨ®еҸҠең°ж–№еӯҰж ЎпјҢд»…дҝқз•ҷеӣҪеӯҗеӯҰдёғеҚҒдәҢеҗҚеӯҰз”ҹпјӣдёүжҳҜеңЁе®ЈеёғеәҹеӯҰ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еҶіе®ҡжҙҫйҒЈдёүеҚҒеҗҚй«ҳеғ§еҫҖе…ЁеӣҪеҚҒдёүдёӘе·һйўҒйҖҒиҲҚеҲ©пјҢд»ҘиЎЁжҳҺж–°зҡ„жІ»еӣҪзҗҶеҝөгҖӮгҖҠйҡӢд№Ұ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йҡӢж–Үеёқд»ҒеҜҝе…ғе№ҙе…ӯжңҲд№ҷдё‘пјҢе…¶ж—ҘпјҢйўҒиҲҚеҲ©дәҺиҜёе·һвҖқгҖӮ
йўҒйҖҒиҲҚеҲ©иҝҷ件дәӢпјҢйҡӢж–ҮеёқжқЁеқҡзӯ№еҲ’дәҶеҫҲй•ҝж—¶й—ҙпјҢе®һж–ҪиҝҮзЁӢдёӯдёҚжғңеҠЁз”ЁеӣҪ家еҠӣйҮҸпјҢжҠ•е…Ҙе·ЁеӨ§дәәеҠӣзү©еҠӣпјҢз”ҡиҮіжҺҖиө·иҪ°иҪ°зғҲзғҲзҡ„еҙҮдҪӣиҝҗеҠЁпјҢжңҹжңӣиҝҷеңәеүҚж— еҸӨдәәзҡ„еҙҮдҪӣиҝҗеҠЁиғҪдёәеӨ§йҡӢзҺӢжңқеёҰжқҘеҘҪиҝҗгҖӮжӯЈжүҖи°“дёҠжңүжүҖеҘҪпјҢдёӢеҝ…з”ҡз„үгҖӮйҡӢж–ҮеёқйўҒйҖҒиҲҚеҲ©пјҢе…ЁеӣҪеҗ„ең°дәүе…ҲжҒҗеҗҺж–°е»әдҫӣеҘүиҲҚеҲ©зҡ„дҪӣеЎ”гҖӮзҹӯзҹӯдёүе№ҙж—¶й—ҙеҶ…пјҢе…ЁеӣҪдҝ®е»әдҪӣеЎ”и¶…иҝҮзҷҫеә§гҖӮ
еңЁиҝҷеңәеЈ°еҠҝжө©еӨ§зҡ„еҙҮдҪӣиҝҗеҠЁдёӯпјҢ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иЎЁзҺ°еҫ—зү№еҲ«жҠўзңјгҖӮ(жҳҺ)гҖҠеҜ°е®ҮйҖҡеҝ—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йҡӢж–Үеёқ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пјҢеңЁжӯҰжҳҢеҺҝдёңеҚҒйҮҢгҖӮиғңзјҳеҜәи®°дә‘пјҢйҡӢд»ҒеҜҝеҲқпјҢж–Үеёқд»ҘйҮҠиҝҰеҰӮжқҘж„ҹеә”иҲҚеҲ©еҲҶеёғеӨ©дёӢпјҢе»әеЎ”зҷҫжүҖгҖӮжҳҜеЎ”дёәеӨ©дёӢ第дәҢгҖӮвҖқжё…д»Је…үз»Ә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д№ҹжңү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йҡӢ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еңЁеҺҝдёңеҚҒйҮҢгҖӮиғңзјҳеҜәи®°пјҢйҡӢд»ҒеҜҝеҲқпјҢж–Үеёқд»ҘеҰӮжқҘж„ҹеә”иҲҚеҲ©еҲҶеёғеӨ©дёӢпјҢе»әеЎ”зҷҫжүҖпјҢжӯӨдёә第дәҢгҖӮвҖқ
(жҳҺ)гҖҠеҜ°е®ҮйҖҡеҝ—гҖӢ жҲҗд№ҰдәҺжҳҺжҷҜжі°дёғе№ҙпјҢеҚі1456е№ҙпјҢиҜҘеҝ—жәҗиҮӘжҙӘжӯҰдёүе№ҙпјҲ1370е№ҙпјүз”ұйӯҸдҝҠж°‘зӯүжҢүгҖҠеӨ§е…ғеӨ§дёҖз»ҹеҝ—гҖӢдҪ“дҫӢзәӮжҲҗзҡ„гҖҠеӨ§жҳҺеҝ—д№ҰгҖӢпјҢеӣ жӯӨе…¶дёӯи®°иҪҪзҡ„еҶ…е®№дҫқжҚ®йғҪжҳҜжё…жҷ°еҸҜйқ зҡ„гҖӮйҖҸиҝҮдёҠиҝ°жӯҰжҳҢеҺҝдёңеҚҒйҮҢйҡӢ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зҡ„е…·дҪ“и®°иҪҪпјҢд»ҠеӨ©дҫқзЁҖиҝҳиғҪзңӢеҲ°йҡӢеҲқдҪӣж•ҷеңЁ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ең°еҢәзҡ„йјҺзӣӣеұҖйқўпјҢж„ҹеҸ—еҲ°еҺҶеҸІдёҠ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ең°еҢәдҪӣж•ҷдј ж’ӯзҡ„е·ЁеӨ§еҪұе“ҚеҠӣгҖӮ
йҰ–е…ҲпјҢйҡӢж–ҮеёқйўҒйҖҒиҲҚеҲ©зҡ„еҜ№иұЎпјҢзҡҶдёәвҖңеӨ©дёӢеҗҚи—©вҖқгҖӮпјҲе®ӢпјүйҮҠеҝ—зЈҗж’°гҖҠдҪӣзҘ–з»ҹи®°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д»ҒеҜҝе…ғе№ҙпјҲе…¬е…ғ601е№ҙпјүпјҢиҜҸеӨ©дёӢеҗҚи—©е»әзҒөеЎ”пјҢйҒЈжІҷй—ЁеҮҖдёҡгҖҒзңҹзҺүзӯүеҲҶйҖҒиҲҚеҲ©пјҢеҘүи—ҸиҜёйғЎзҷҫдёҖеҚҒеЎ”гҖӮвҖқйҡӢеҲқй„Ӯе·һжІ»жүҖеңЁд»ҠеӨ©зҡ„жӯҰжҳҢпјҢиҖҢеҪ“ж—¶зҡ„жӯҰжҳҢе·Із»ҸеҸӘжҳҜйҡ¶еұһдәҺй„Ӯе·һзҡ„дёҖдёӘеҺҝгҖӮйҡӢж–ҮеёқйўҒйҖҒиҲҚеҲ©дҫӣеҘүеңЁе·Із»Ҹж’ӨйғЎеӯҳеҺҝзҡ„жӯҰжҳҢпјҢдёҚиғҪдёҚиҜҙе…·жңүзү№еҲ«зҡ„иұЎеҫҒж„Ҹд№үгҖӮ
йҡӢе№ійҷҲ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ӯҰжҳҢдҪңдёәжӣҫз»Ҹзҡ„дёүеӣҪеҗҙйғҪгҖҒдёӨжҷӢйҮҚй•ҮпјҢд№ҹжҳҜйҡӢж–Үеёқз»Ҹз•ҘжұҹеҚ—зҡ„йҮҚиҰҒжЎҘеӨҙе ЎпјҢжҲҳз•Ҙең°дҪҚзҡ„жһҒз«ҜйҮҚиҰҒжҖ§дёҚиЁҖиҖҢе–»гҖӮгҖҠйҡӢд№ҰВ·е‘Ёжі•е°ҡдј гҖӢдёӯжңүдёҖж®өи®°иҪҪпјҡвҖңеІҒйҰҖпјҢиҪ¬й»„е·һжҖ»з®ЎпјҢдёҠйҷҚеҜҶиҜҸпјҢдҪҝз»Ҹз•ҘжұҹеҚ—пјҢдјәеҖҷеҠЁйқҷгҖӮеҸҠдјҗйҷҲд№ӢеҪ№пјҢд»ҘиЎҢеҶӣжҖ»з®Ўйҡ¶з§ҰеӯқзҺӢпјҢзҺҮиҲҹеёҲдёүдёҮеҮәдәҺжЁҠеҸЈпјҢйҷҲеҹҺе·һеҲәеҸІзҶҠй—Ёи¶…еҮәеёҲжӢ’жҲҳпјҢеҮ»з ҙд№ӢпјҢж“’и¶…дәҺйҳөпјҢиҪ¬й„Ӯе·һеҲәеҸІвҖқгҖӮиҝҷйҮҢд»Ӣз»ҚдәҶйҡӢж–Үеёқз”Ёе…«е№ҙзӯ№еҲ’пјҢд»…з”ЁдёӨдёӘжңҲе°ұе®һзҺ°дәҶе№ійҷҲеӨ§дёҡпјҢеҪ“ж—¶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жІҝжұҹе°ұжҳҜйҡӢеҶӣй•ҝжңҹз»Ҹз•Ҙзҡ„йҮҚиҰҒзӘҒз ҙеҸЈгҖӮ
дёҺжӯӨеҗҢж—¶пјҢдҪӣж•ҷз»Ҹ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еҗ‘жұҹеҚ—зҡ„дј ж’ӯеҪұе“ҚеҠӣе·ЁеӨ§гҖӮдҪңдёәжұҹеҚ—дҪӣж•ҷеҲқдј д№Ӣең°пјҢд»Һжұүжң«ж”Ҝи°ҰиҜ‘з»ҸпјҢдёүеӣҪз»ҙзҘҮйҡҫз«әеҫӢзӮҺз»“дјҙжқҘй©»пјҢдёӨжҷӢйҷ¶дҫғйҖҒеғҸгҖҒж…§иҝңиҘҝеұұй©»й”ЎпјҢеҚ—жңқйҪҗж—¶жі•жҷӨжЁҠеұұдҝ®иЎҢпјҢеҺҝеҶ…дёҚд»…дҪӣж•ҷеҜәеәҷйҒҚеёғпјҢе…¶дёӯеҗүзҘҘеҜәжҚ®дј иҝҳдёҺж–ҮеёқжңүзқҖзӣҙжҺҘе…ізі»гҖӮе…үз»Ә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иҪҪпјҡвҖңеҗүзҘҘеҜәеңЁеҺҝиҘҝдә”йҮҢгҖӮйҡӢж–ҮеёқжңӘиҙөж—¶пјҢеёёиҲҹиЎҢжұҹдёӯгҖӮеӨңжіҠдёӯпјҢжўҰж— е·ҰжүӢпјҢеҸҠи§үпјҢз”ҡжҒ¶д№ӢгҖӮеҸҠзҷ»еІёпјҢиҜЈдёҖиҚүеәөдёӯпјҢжңүдёҖиҖҒеғ§пјҢйҒ“жһҒй«ҳгҖӮдҝұд»ҘжўҰе‘Ҡд№ӢгҖӮеғ§иө·иҙәжӣ°пјҡж— е·ҰжүӢиҖ…пјҢзӢ¬жӢід№ҹгҖӮеҪ“дёәеӨ©еӯҗгҖӮеҗҺеёқе…ҙпјҢе»әжӯӨеәөдёәеҗүзҘҘеҜәгҖӮеұ…жӯҰжҳҢдёӢдёүеҚҒйҮҢгҖӮвҖқеҺҝеҝ—иҝӣдёҖжӯҘеј•гҖҠзӢ¬ејӮеҝ—гҖӢи®°иҪҪпјҡе®Ӣеј иҲңж°‘пјҢе…ғдё°зҷёдәҘз§ӢеӯЈпјҢиөҙе®ҳжҹіеІӯиҲЈиҲҹжЁҠеҸЈпјҢдёҺжҪҳеҪҰжҳҺгҖҒиҢғдәӯзҲ¶д»Ҙе°ҸиүҮиҝҮеҗүзҘҘеҜәгҖӮжҳҜж—ҘеӨ§йЈҺйӣЁйӣӘпјҢдҪңпјҡвҖңжұҹдёҠз§ӢйЈҺд№қж—ҘеҜ’пјҢж•…дәәе°Ҡй…’жҡӮзӣёж¬ўгҖӮеҰӮдҪ•еЎһеҢ—ж— з©·йӣӘпјҢеҚҙеқҗжЁҠеұұз«№дёҮз«ҝгҖӮвҖқеҗүзҘҘеҜәеҲ°е®Ӣд»Је…ғдё°е№ҙй—ҙд»Қ然еӯҳеңЁгҖӮ
е…¶ж¬ЎпјҢдёүеҚҒеҗҚй«ҳеғ§еҫҖе…ЁеӣҪеҚҒдёүдёӘе·һйўҒйҖҒиҲҚеҲ©пјҢиў«и§ҶдёәеҚҒеҲҶзҘһеңЈиҖҢеә„дёҘзҡ„дҪҝе‘ҪгҖӮеҗ„и·Ҝй«ҳеғ§еҮәеҸ‘еүҚж–ҮеёқйғҪиҰҒдәІжҺҲзҒөйӘЁпјҢдҪіиЁҖеӢүеҠұпјҢж…°й—®дјҳжёҘпјҢеҗҢж—¶иҝҳд»Өеҗ„ең°е®ҳе‘ҳе–„еҠ жҺҘеҫ…гҖӮеҗ„ең°жҺҘеҸ—иҲҚеҲ©жӣҙжҳҜи§ҶдёәеӨ§еҗүпјҢйҖ еЎ”дҫӣеҘүдёҚж•ўжңүдёқжҜ«ж…ўжҖ гҖӮжӯҰжҳҢйҡӢж–Үеёқ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пјҢвҖңжҳҜеЎ”дёәеӨ©дёӢ第дәҢвҖқгҖҒвҖңе»әеЎ”зҷҫжүҖпјҢжӯӨдёә第дәҢвҖқпјҢе…¶дёӯиҮіе°‘йҡҗеҗ«еҮ дёӘж–№йқўеҸҜиғҪзҡ„и§ЈиҜ»гҖӮеҸҜиғҪжҳҜвҖңиҜёйғЎзҷҫдёҖеҚҒеЎ”вҖқдёӯж—¶й—ҙдёҠ第дәҢдёӘе»әжҲҗзҡ„йҡӢ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пјҢеҸҜиғҪжҳҜвҖңиҜёйғЎзҷҫдёҖеҚҒеЎ”вҖқдёӯ规模жҲ–еҪұе“Қ第дәҢзҡ„йҡӢ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пјҢд№ҹеҸҜиғҪжҳҜвҖңиҜёйғЎзҷҫдёҖеҚҒеЎ”вҖқдёӯиў«йҡӢж–ҮеёқиӮҜе®ҡдёәеӨ©дёӢ第дәҢзҡ„йҡӢ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гҖӮжҖ»д№ӢпјҢдёҚз®ЎжҳҜе“ӘдёҖз§Қи§ЈиҜ»пјҢеӨ©дёӢ第дәҢеЎ”пјҢйғҪиҜҙжҳҺжӯҰжҳҢеҺҝзҡ„йҡӢж–Үеёқ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еңЁеҪ“ж—¶е…ЁеӣҪиҪ°иҪ°зғҲзғҲзҡ„еҙҮдҪӣиҝҗеҠЁдёӯең°дҪҚжһҒй«ҳпјҢеңЁйҡӢж–Үеёқ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дёӯзҡ„еҪұе“ҚеҠӣжһҒеӨ§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д№ҹд»ҺдёҖдёӘдҫ§йқўиҜҙжҳҺпјҢйҡӢеҲқжӯҰжҳҢзҡ„дҪӣж•ҷдј ж’ӯжҙ»еҠЁпјҢд»Қ然зӣӣеҶөдёҚеҮҸд»ҺеүҚгҖӮ
第дёүпјҢйҡӢж–Үеёқ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д»ҘеӨ–пјҢеңЁж•ҙдёӘйҡӢе”җжңҹй—ҙжҲҗдёәжӯҰжҳҢең°еҢәдҪӣж•ҷдј ж’ӯзӣӣжһҒдёҖж—¶зҡ„иұЎеҫҒгҖӮйҡӢе”җд№Ӣй—ҙпјҢжӯҰжҳҢең°еҢәзҡ„дҪӣж•ҷдј ж’ӯе‘ҲзҺ°еҮ дёӘзӘҒеҮәзү№еҫҒгҖӮдёҖжҳҜеҹҺд№ЎйҒҚеёғгҖӮйҡӢе”җжңҹй—ҙжӯҰжҳҢең°еҢәи§ҒиҜёж–ҮзҢ®и®°иҪҪзҡ„еҜәеәҷи¶…иҝҮ20еӨҡеӨ„гҖӮиғңзјҳеҜәпјҲйҡӢпјүгҖҒеҗүзҘҘеҜәпјҲйҡӢпјүгҖҒжҖҖжҒ©еҜәпјҲе”җпјҢзҘһеұұд№Ўиҹ йҫҷеұұпјүгҖҒж–°е–ң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зҘһеұұд№ЎпјүгҖҒе®ҒеӣҪ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йҮ‘зүӣпјүгҖҒжі—жҙІйҷўпјҲе”җгҖҒйҮ‘зүӣиЎ—пјүгҖҒжё…еі°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з¬Ұзҹід№ЎпјүгҖҒжі•еҚҺ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зҒөжәӘд№ЎжңЁйұјеұұпјүгҖҒз»Қе…ҙ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马иҝ№д№Ўй©¬иҝ№еұұпјүгҖҒзҒөеұұ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зҒөжәӘд№ЎзҒөжәӘеұұпјүгҖҒж–—еұұ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иҙӨеәҫд№Ўж–—еұұпјүгҖҒе®ҸеҢ–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дёңж–№еұұпјүгҖҒзҒө鹫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зҷҪйӣүеұұпјүгҖҒеҮӨеҮ°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еҮӨеҮ°еұұпјүгҖҒеӨ©еҸ°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еӨ§еҶ¶пјүгҖҒйҡҶжөҺ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еӨ§еҶ¶пјүгҖҒж –йҡҗ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еӨ§еҶ¶пјүгҖҒйҡҶзӘҹ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еӨ§еҶ¶пјүгҖҒе№ҝжі•еҜәпјҲйҡӢе”җгҖҒеӨ§еҶ¶пјүгҖҒйҡҶеә”еҜәпјҲе”җгҖҒеӨ§еҶ¶пјүзӯүзӯүгҖӮп№қ53п№һеңЁжЁҠеұұд№ӢеӨ–пјҢеўғеҶ…еҗҚеұұиғңиҝ№еҮ д№ҺйғҪжңүдҪӣж•ҷеҜәеәҷгҖӮдәҢжҳҜеҪұе“ҚеҠӣйҷҚдҪҺгҖӮйҡӢе”җејҖе§ӢпјҢжӯҰжҳҢеңЁжңқе»·жІ»зҗҶдҪ“зі»дёӯзҡ„ең°дҪҚдёӢйҷҚпјҢд»Һжӣҫз»Ҹзҡ„дёүеӣҪеҗҙйғҪгҖҒдёӨжҷӢйҮҚй•ҮгҖҒеҗҚйғЎжңӣйӮ‘пјҢдёҖжӯҘеҸҳжҲҗдёҖдёӘжҷ®йҖҡзҡ„еҺҝгҖӮеўғеҶ…дҪӣж•ҷеҜәеәҷ规模йғҪдёҚжҳҜеҫҲеӨ§пјҢй«ҳеғ§еӨ§еҫ·зҡ„еҫҖжқҘж„ҲеҸ‘йІңи§ҒпјҢеҪұе“ҚеҠӣд№ҹе·Із»ҸдёҚеӨҚд»ҺеүҚгҖӮз»ӯи®°еҚ—жңқжўҒд»ҘеҗҺй«ҳеғ§еӨ§еҫ·зҡ„гҖҠе”җй«ҳеғ§дј гҖӢгҖҒгҖҠе®Ӣй«ҳеғ§дј гҖӢпјҢе·Із»ҸдёҚи§ҒжӯҰжҳҢең°еҢәжңүеҗҚеҜәй«ҳеғ§еҲ—иҝ°е…¶дёӯгҖӮеҗҚйҮҚдёҖж—¶зҡ„жӯҰжҳҢйҡӢж–Үеёқ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пјҢд»ҘеҸҠеҺҶеҸІжӮ д№…зҡ„жҳҢд№җеҜәгҖҒеҜ’жәӘеҜәгҖҒиҘҝеұұеҜәзӯүзӯүпјҢеңЁе”җжң«вҖңдјҡжҳҢжі•йҡҫвҖқзҡ„иҝҮзЁӢеҪ“дёӯжӣҙжҳҜиў«жҜҒдәҺдёҖж—ҰгҖӮ
дҪӣж•ҷдј е…ҘдёӯеӣҪд»ҘеҗҺпјҢжӣҫз»ҸйҒӯйҒҮиҝҮеӣӣж¬Ўжі•йҡҫпјҢжүҖи°“вҖңдёүжӯҰдёҖе®—д№ӢеҺ„вҖқгҖӮеҲҶеҲ«жҳҜеҢ—йӯҸеӨӘжӯҰеёқжӢ“и·Ӣз„ҳжҜҒдҪӣгҖҒеҢ—е‘ЁжӯҰеёқе®Үж–ҮйӮ•жҜҒдҪӣгҖҒе”җжӯҰе®—жқҺзӮҺжҜҒдҪӣгҖҒе‘Ёдё–е®—жҹҙиҚЈжҜҒдҪӣгҖӮдёҚиҝҮеңЁеӣӣж¬Ўжі•йҡҫеҪ“дёӯпјҢжңүдёүж¬ЎжӯҰжҳҢең°еҢәжңӘжӣҫж¶үеҸҠгҖӮе…¶дёӯеҢ—йӯҸжӯҰеёқе’ҢеҢ—е‘ЁжӯҰеёқдёӨж¬ЎжҜҒдҪӣпјҢеҚ—ж–№ең°еҢәжңӘеҸ—зӣҙжҺҘеҶІеҸҠгҖӮдә”д»ЈеҗҺжңҹе‘Ёдё–е®—жҜҒдҪӣпјҢеҪ“ж—¶зҡ„жӯҰжҳҢд№ҹдёҚеңЁе…¶жІ»дёӢгҖӮе”җжң«вҖңдјҡжҳҢжі•йҡҫвҖқпјҢжҳҜ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дҪӣж•ҷдј ж’ӯиҝҮзЁӢдёӯеҸ—еҲ°еҶІеҮ»зҡ„е”ҜдёҖдёҖж¬ЎпјҢд№ҹжҳҜд»Һж №жң¬дёҠж”№еҸҳдҪӣж•ҷеңЁй„Ӯе·һдј ж’ӯеҺҶеҸІзҡ„е”ҜдёҖдёҖж¬ЎгҖӮ
е”җжңқеҗҺжңҹжӯҰе®—жқҺзӮҺеңЁдҪҚжңҹй—ҙпјҢйҖҡиҝҮеҠ ејәдёӯеӨ®йӣҶжқғпјҢйҖ е°ұвҖңдјҡжҳҢдёӯе…ҙвҖқзӣӣдё–гҖӮдҪҶжқҺзӮҺжң¬дәәеҙҮдҝЎйҒ“ж•ҷпјҢж·ұжҒ¶дҪӣж•ҷгҖӮжӯӨж—¶пјҢе…ЁеӣҪдёҠдёӢжңүеӨ§дёӯеһӢдҪӣж•ҷеҜәйҷўиҝ‘5000еә§пјҢе°ҸеһӢеәҷе®ҮжӣҙеӨҡиҫҫ4дёҮдҪҷеә§пјҢеңЁеҶҢеғ§е°јиҝ‘30дёҮдәәпјҢеҜәйҷўеҘҙйҡ¶иҫҫ15дёҮд№Ӣдј—гҖӮе…ЁеӣҪеҜәйҷўеҚ жңүиүҜз”°ж•°еҚҒдёҮдә©пјҢеҪўжҲҗдёҖдёӘеҸҲдёҖдёӘзӣёеҜ№е°Ғй—ӯзҡ„еә„еӣӯпјҢеҜәйҷўеҶ…йғЁзҡ„з»ҸжөҺеӨ§жқғжҺҢжҸЎеңЁдҪҸжҢҒжүӢдёӯгҖӮеғ§е°јжһҒе°‘иҖ•з§ҚпјҢиҖҢйқ еҶңж°‘иҖ•з§Қеңҹең°д»Ҙ收еҸ–ең°з§ҹпјҢжҲ–еҸ‘ж”ҫй«ҳеҲ©иҙ·дҪңдёәз»ҸжөҺжқҘжәҗгҖӮдјҡжҳҢдәҢе№ҙпјҢеҚіе…¬е…ғ842е№ҙпјҢе”җжӯҰе®—жқҺзӮҺи®ҫж–Ӣе®ҙпјҢиҜ·еғ§дәәгҖҒйҒ“еЈ«и®Іжі•пјҢз»“жқҹеҗҺдёӨеҗҚйҒ“еЈ«иў«иөҗзҙ«пјҢдҪӣй—Ёй«ҳеғ§еҚҙз©әжүӢиҖҢеҪ’гҖӮе”җжңқдёүе“Ғд»ҘдёҠзҡ„е®ҳжңҚдёәзҙ«иүІпјҢиөҗзҙ«ж„Ҹе‘ізқҖдёӨеҗҚйҒ“еЈ«дҪҚеҗҢдёүе“ҒгҖӮеҪ“ж—¶еңЁдёӯеӣҪдј жі•зҡ„дёҖдҪҚеӨ©з«әеғ§дәәеҗ¬й—»жӯӨдәӢжһҒдёәдёҚж»ЎпјҢжңӘз»ҸеҸ¬и§ҒпјҢж“…й—ҜзҡҮе®«иҰҒжұӮйқўи§Ғе”җжӯҰе®—пјҢиҜ·жұӮеӣһеҪ’жң¬еӣҪгҖӮеӨ©з«әеғ§дәәзҡ„зӢӮеҰ„е’ҢеӮІж…ўпјҢеңЁжӯҰе®—еҝғдёӯеҹӢдёӢдәҶжңҖз»ҲзҒӯдҪӣзҡ„з§ҚеӯҗгҖӮеҗҢе№ҙпјҢжӯҰе®—дёӢд»ӨпјҢеҮЎжңүиҝқзҠҜдҪӣж•ҷ清规жҲ’еҫӢзҡ„еғ§е°јпјҢеҝ…йЎ»иҝҳдҝ—пјҢжңүиҙўдә§иҖ…没收гҖӮдёҚж„ҝ没收иҖ…пјҢиҝҳдҝ—еҗҺдәӨдёӨеҖҚиөӢзЁҺгҖӮдјҡжҳҢдёүе№ҙпјҢеҚіе…¬е…ғ843е№ҙпјҢе”җжӯҰе®—еҗ¬й—»жңүи—©й•ҮеҘёз»ҶеҒҮжү®еғ§дәәи—ҸеңЁдә¬еёҲпјҢдәҺжҳҜдёӢвҖңжқҖжІҷй—Ёд»ӨвҖқпјҢй•ҝе®үеҹҺдёӯ300еӨҡеҗҚеғ§дҫЈиў«жқҖгҖӮдјҡжҳҢдә”е№ҙпјҢеҚіе…¬е…ғ845е№ҙпјҢе”җжӯҰе®—еҸҲдёӢд»Өжё…жҹҘе…ЁеӣҪеҜәйҷўеҸҠеғ§дҫЈдәәж•°пјҢжӢҶжҜҒеҜәеәҷ4600дҪҷеә§е’Ңз§Ғз«Ӣеғ§еұ…еӣӣдёҮеӨҡжүҖпјҢеҺҶеҸІдёҠиў«з§°дёәвҖңдјҡжҳҢжі•йҡҫвҖқгҖӮе”җжӯҰе®—жқҺзӮҺејҖеұ•зҡ„зҒӯдҪӣиҝҗеҠЁжҳҜеҺҶеҸІдёҠеӣӣж¬ЎзҒӯдҪӣиҝҗеҠЁдёӯ规模жңҖеӨ§гҖҒеҪұе“ҚжңҖе№ҝзҡ„зҒӯдҪӣиҝҗеҠЁгҖӮд№ҹжҳҜе”ҜдёҖдёҖж¬ЎеҸ‘з”ҹеңЁеӣҪ家稳е®ҡгҖҒж”ҝеұҖдёӯе…ҙж—¶жңҹзҡ„зҒӯдҪӣиҝҗеҠЁгҖӮ
е”җжӯҰе®—еәҹйҷӨдҪӣж•ҷиҝҗеҠЁпјҢеҸӨд»ЈжӯҰжҳҢең°еҢәдҪӣж•ҷдј ж’ӯжүҖеҸ—еҶІеҮ»еҪұе“Қж·ұиҝңгҖӮеҪ“ж—¶жңқе»·иҜҸд»ӨпјҢй•ҝе®үгҖҒжҙӣйҳіе·ҰеҸіиЎ—еҗ„з•ҷдәҢеҜәпјҢжҜҸеҜәеғ§еҗ„дёүеҚҒдәәгҖӮеӨ©дёӢиҜёйғЎеҗ„з•ҷдёҖеҜәпјҢеҜәеҲҶдёүзӯүпјҢдёҠгҖҒдёӯгҖҒдёӢеҜәеҗ„дҝқз•ҷдәҢеҚҒдәәгҖҒеҚҒдәәгҖҒдә”дәәгҖӮе…¶д»–еӨ©дёӢиҜёеҜәйҷҗжңҹжӢҶйҷӨгҖӮе…¶ж—¶жӯҰжҳҢ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ҷ®йҖҡеҺҝпјҢеўғеҶ…еӨҡеә§еҜәгҖҒеЎ”дёҖж— е№ёе…ҚпјҢдҪӣж•ҷдј ж’ӯеӣ жӯӨе…ғж°”еӨ§дјӨгҖӮеҪ“ж—¶иҜ—еғ§йҪҗе·ІеңЁгҖҠд№ұеҗҺз»ҸиҘҝеұұеҜәгҖӢдёҖиҜ—еҶҷйҒ“пјҡвҖңжқҫзғ§еҜәз ҙжҳҜеҲҖе…өпјҢи°·еҸҳйҷөиҝҒдәӢеҸҜжғҠпјҢдә‘йҮҢд№ҚйҖўж–°дҪҸдё»пјҢзҹіиҫ№йҮҚи®Өж—§йўҳеҗҚгҖӮй—ІдёҙиҸЎиҗҸиҚ’жұ еқҗпјҢд№ұиёҸйёійёҜз ҙз«№иЎҢпјҢж¬Ідјҙй«ҳеғ§йҮҚз»“зӨҫпјҢжӯӨиә«ж— и®ЎиҲҚеүҚзЁӢгҖӮвҖқйҖҸиҝҮиҜ—еғ§зҡ„з®ҖеҚ•жҸҸеҶҷпјҢеҪ“ж—¶жӯҰжҳҢең°еҢәдҪӣж•ҷжүҖеҸ—еҶІеҮ»зҡ„жҷҜиұЎеҸҜи§ҒдёҖж–‘гҖӮй„Ӯе·һзҺ°еӯҳзҡ„еҸӨд»ЈжӯҰжҳҢеҸІеҝ—ж–ҮзҢ®пјҢйғҪдёҚи§Ғжңүе…ійҡӢж–Үеёқ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й“ӯгҖҒиғңзјҳеҜәзҡ„и®°иҪҪгҖӮеҸӨд»ЈжӯҰжҳҢең°ж–№еҝ—еҸҠеҗ„зұ»ж–ҮеҫҒ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йҡӢж–Үеёқ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й“ӯж–ҮгҖҒиғңзјҳеҜәи®°д№Ӣзұ»зҡ„и®°еҪ•гҖӮеҪ“ж—¶зҡ„жӯҰжҳҢеҺҝдёңеҚҒйҮҢпјҢеә”иҜҘеңЁд»ҠеӨ©зҡ„й„Ӯе·һеҹҺеҢәжҙӢжҫңж№–дёңеҢ—еІёгҖҒеҸёеҫ’еәҷдёҖеёҰпјҢиҝҷйҮҢд»ҠеӨ©е№¶жІЎжңүз•ҷдёӢйҡӢж–ҮеёқиҲҚеҲ©зҹіеЎ”гҖҒиғңзјҳеҜәзҡ„д»»дҪ•иёӘиҝ№пјҢе·Із»Ҹе®Ңе…ЁеҹҺеёӮиЎ—еҢәеҢ–гҖӮйҡӢе”җжӯҰжҳҢвҖңеӨ©дёӢ第дәҢеЎ”вҖқпјҢвҖңдјҡжҳҢжі•йҡҫвҖқд»ҘеҗҺпјҢе·ІжҲҗдёәж–ӯж–ӯз»ӯз»ӯеҮәзҺ°еңЁе°‘ж•°ж–ҮзҢ®дёӯзўҺзүҮеҢ–зҡ„еҺҶеҸІи®°еҝҶгҖӮ
е®Ӣе…ғж—¶жңҹпјҢй„Ӯе·һжҜ”иҫғи‘—еҗҚзҡ„дҪӣж•ҷеҜәеәҷеҸӘжңүй•ҝе…ҙеҜәпјҢеҙҮзҰҸеҜәпјҢеҰҷе–ңеҜәпјҢйҫҷиҹ зҹ¶еҜәеҮ еӨ„гҖӮй•ҝе…ҙеҜәеңЁеҺҹзҒөжәӘд№ЎиҺІиҠұеұұпјҢе®Ӣе’ёе№іж—¶е»әгҖӮеҙҮзҰҸеҜәеңЁеҺҹзҒөжәӘд№Ўжё…ж°ҙжҪӯгҖӮеҰҷе–ңеҜәеңЁеҺҝдёңпјҢеҚ—е®Ӣжі°е§Ӣй—ҙдә”зҘ–жј”зҰ…еёҲе»әгҖӮе…ғд»Јдҝ®е»әзҡ„йҫҷиҹ зҹ¶еҜәпјҢж—§еҗҚи§ӮйҹійҳҒпјҢе…ғд»Јжң«жңҹе»әпјҢжҳҺејҳжІ»гҖҒеҳүйқ–е№ҙй—ҙеӨҡж¬ЎеӢҹиө„йҮҚдҝ®гҖӮи§ӮйҹійҳҒзӢ¬з«ӢжұҹиЎЁпјҢеіҷз«ӢжұҹдёӯпјҢд№ғдёҮйҮҢй•ҝжұҹд№ӢиғңжҷҜгҖӮжҳҺжё…д№Ӣй—ҙпјҢй„Ӯе·һжӣҫеӨ§е…ҙеңҹжңЁпјҢйҮҚдҝ®гҖҒж–°е»әеҜ’жәӘеҜәгҖҒиҘҝеұұеҜәзӯүеӨ§е°ҸеҜәеәҷгҖӮжҖ»дҪ“иҖҢиЁҖпјҢз»ҸиҝҮе”җд»Јжҷҡжңҹзҡ„вҖңдјҡжҳҢжі•йҡҫвҖқпјҢй„Ӯе·һпјҲеҸӨжӯҰжҳҢпјүдҪӣж•ҷзҡ„дј ж’ӯпјҢе·Із»Ҹе®Ңе…ЁдёҚеӨҚд»ҺеүҚзӣӣеҶөгҖӮ
дҪңиҖ…пјҡжҘҡжҳ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