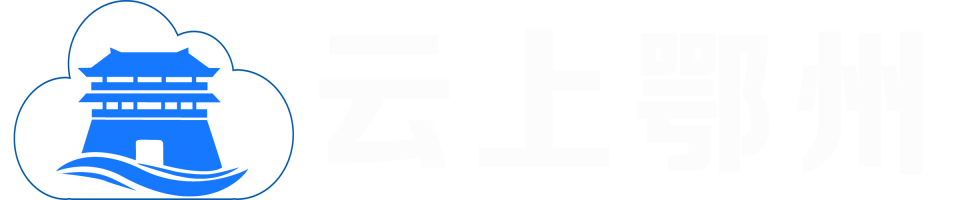дҪҷдёүжҜӣпјҡи®°еҪ•еҺҶеҸІдј жүҝж–ҮжҳҺ
в–ЎдҪ•еұ№з„¶пјҲжӯҰжұүеӨ§еӯҰж–°й—»дёҺдј ж’ӯеӯҰзЎ•еЈ«пјү
иҮӘй„Ӯе·һе»әеёӮд»ҘжқҘпјҢе·ІжңүдёҚе°‘дјҳз§Җзҡ„ең°ж–№еҝ—д№Ұж¶ҢзҺ°еҮәжқҘпјҢе®ғ们еңЁдёәй„Ӯе·һз»ҸжөҺеҸ‘еұ•жңҚеҠЎ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жӣҙдҪңдёәж–ҮеҢ–дј жүҝзҡ„иЎҖи„үиҖҢжҳҫеҫ—ејҘи¶ізҸҚиҙөгҖӮйӮЈд№ҲпјҢеңЁиҝҷдәӣең°ж–№еҝ—д№ҰеҶҷзҡ„иғҢеҗҺпјҢжҳҜеҗҰжңүдёҖдёӘжё…жҷ°иҖҢе®Ңж•ҙзҡ„еҝ—д№Ұзј–зәӮи®ЎеҲ’пјҢе®ғ们дёәдҪ•иҖҢдҪңпјҢеҰӮдҪ•жҺЁиҝӣпјҢеҸҲз»ҸеҺҶдәҶжҖҺж ·зҡ„йҳ¶ж®өпјҹдёәи§Јзӯ”з–‘й—®пјҢжҲ‘们йҮҮи®ҝдәҶй„Ӯе·һеёӮжЎЈжЎҲйҰҶеүҜйҰҶй•ҝдҪҷдёүжҜӣпјҢиҜ•еӣҫд»Һе®Ҹи§ӮеұӮйқўжҸҸз»ҳй„Ӯе·һдҝ®еҝ—еҺҶзЁӢзҡ„еӨ§иҮҙиҪ®е»“гҖӮ
зӣӣдё–е§Ӣдҝ®еҝ—
ж”ҫзңје…ЁеӣҪпјҢеҗ„дёӘең°еҢәж–№еҝ—зҡ„е…ҙдҝ®еҹәжң¬дёҠжҳҜд»ҺдёҠдё–зәӘ80е№ҙд»ЈеҲқгҖҒ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еҲқжңҹзқҖжүӢејҖеұ•зҡ„гҖӮвҖңзӣӣдё–е§Ӣдҝ®еҝ—пјҢеҸӘжңүеңЁе’Ңе№іе№ҙд»ЈпјҢзј–зәӮеҝ—д№ҰжүҚиғҪеҫ—д»ҘејҖеұ•пјҢ并еҸ‘жҢҘе…¶д»·еҖјгҖӮвҖқдҪҷдёүжҜӣиҜҙпјҢйӮЈж—¶еҖҷеӣҪ家ејҖе§ӢеҜ№ең°ж–№зҡ„еҝ—д№Ұзј–зәӮжҸҗеҮәиҰҒжұӮпјҢ并дёӢиҫҫзӣёе…іж–Ү件пјҢд»ҘжҢҮеҜјеҗ„зә§ж”ҝеәңз»„з»ҮиҝӣиЎҢж–№еҝ—зј–и®ўгҖӮ
1984е№ҙ6жңҲ21ж—ҘпјҢй„Ӯе·һеёӮдәәж°‘ж”ҝеәңеҶіе®ҡжҲҗз«Ӣй„Ӯе·һеёӮең°ж–№еҝ—зј–зәӮ委е‘ҳдјҡпјҢдёәеёӮж”ҝеәңеҶ…и®ҫжңәжһ„пјҢеёӮй•ҝжҢӮеё…д»»дё»д»»пјҢеёӮзӣҙдё»иҰҒйғЁй—ЁиҙҹиҙЈдәәдёәжҲҗе‘ҳпјҢй„Ӯе·һең°ж–№еҝ—е·ҘдҪңжңәжһ„з”ұжӯӨе»әз«Ӣиө·жқҘгҖӮ30еӨҡе№ҙжқҘпјҢеҺҶз»ҸеӨҡж¬Ўжңәжһ„ж”№йқ©пјҢй„Ӯе·һеёӮең°ж–№еҝ—дәӢдёҡ并жңӘеҒңж»һпјҢеҸҚиҖҢжҳҫзҺ°еҮәзҷҫиҠұйҪҗж”ҫзҡ„жҖҒеҠҝгҖӮиҝҷдёҖж–№йқўжқҘжәҗдәҺеёӮ委гҖҒеёӮж”ҝеәңйўҶеҜјзҡ„й«ҳеәҰйҮҚи§Ҷпј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д№ҹдёҺең°ж–№еҝ—зј–зәӮе·ҘдҪңиҖ…зҡ„иёҸе®һиӢҰе№ІеҲҶдёҚејҖгҖӮ
дёӨиҪ®дҝ®еҝ—йҳ¶ж®ө
й„Ӯе·һеёӮең°ж–№еҝ—дҝ®и®ўз»ҸеҺҶдәҶдёӨдёӘйҳ¶ж®өпјҢд№ҹз§°вҖңдёӨиҪ®дҝ®еҝ—вҖқпјҢжҜҸдёҖиҪ®зҡ„й—ҙйҡ”ж—¶й—ҙдёә20е№ҙгҖӮе…¶дёӯйңҖиҰҒиҜҙжҳҺзҡ„жҳҜпјҢз”ұдәҺж–°дёӯеӣҪжҲҗз«Ӣд»ҘжқҘеҲ°1984е№ҙпјҢй„Ӯе·һеёӮең°ж–№еҝ—зј–зәӮ委е‘ҳдјҡе»әз«Ӣжңҹй—ҙжІЎжңүдё“й—Ёзҡ„дҝ®еҝ—жңәжһ„пјҢеӣ жӯӨ第дёҖж¬Ўдҝ®еҝ—жІЎжңүдёҘж јжҢүз…§жҜҸ20е№ҙдёҖдҝ®зҡ„ж ҮеҮҶиҝӣиЎҢгҖӮ
第дёҖиҪ®дҝ®еҝ—йҳ¶ж®өдёә1984е№ҙеҲ°1997е№ҙпјҢиҝҷдёӘйҳ¶ж®өзҡ„дё»иҰҒе·ҘдҪңжҳҜе°Ҷжңүи®°иҪҪд»ҘжқҘеҲ°1987е№ҙе…ідәҺй„Ӯе·һеёӮзҡ„жүҖжңүеҺҶеҸІж•ҙзҗҶгҖҒзӯӣйҖүгҖҒзј–зәӮпјҢжіЁйҮҚиҝһз»ӯжҖ§гҖҒе…ЁйқўжҖ§пјҢд»ҘеҪўжҲҗж–°дёӯеӣҪжҲҗз«Ӣд»ҘжқҘ第дёҖйғЁе®Ңж•ҙзҡ„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еҝ—гҖӢгҖӮ第дёҖиҪ®дҝ®еҝ—жңҹй—ҙпјҢе…ЁеёӮеҗ„зӣҙеұһеҚ•дҪҚйғҪз»„е»әдәҶйғЁй—Ёеҝ—еҠһпјҢдё“й—ЁиҙҹиҙЈдҝ®еҝ—е·ҘдҪңпјҢжұҮйӣҶеҗ„йғЁй—Ёжҷәж…§зҡ„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еҝ—гҖӢе…«жҳ“е…¶зЁҝпјҢеҸҚеӨҚжү“зЈЁпјҢжңҖз»ҲдәҺ1997е№ҙеҹәжң¬еҪўжҲҗеҲқзЁҝпјҢ1999е№ҙз”ұдёӯеҚҺд№ҰеұҖжӯЈејҸеҮәзүҲеҸ‘иЎҢпјҢе…Ёд№Ұе…ұ150дёҮеӯ—гҖӮиҝҷдёҖйҳ¶ж®өй—ҙпјҢдҝ®еҝ—е·ҘдҪңиҖ…们еңЁзј–зәӮ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еҝ—гҖӢ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д№ҹйҖҗжӯҘдәҶ解并жҺҢжҸЎдәҶеҝ—д№Ұзҡ„дҪ“дҫӢгҖҒзј–еҶҷзҡ„规иҢғгҖҒиҜӯиЁҖзҡ„йЈҺж јпјҢдёәеҗ„дёӘйғЁй—ЁгҖҒеҗ„дёӘиЎҢдёҡдҝ®и®ўйғЁй—Ёеҝ—гҖҒдё“дёҡеҝ—гҖҒд№Ўй•Үеҝ—жү“дёӢеқҡе®һеҹәзЎҖгҖӮ
第дәҢиҪ®дҝ®еҝ—йҳ¶ж®өдёә2005е№ҙиҮі2016е№ҙпјҢиҝҷдёҖйҳ¶ж®өдё»иҰҒжўізҗҶгҖҒзј–зәӮ1983е№ҙиҮі2007е№ҙзҡ„й„Ӯе·һеҺҶеҸІпјҢеҗҢж—¶ејҖеұ•й„Ӯе·һеёӮдёӢиҫ–еҢәзҡ„еҝ—д№Ұзј–зәӮе·ҘдҪңгҖӮ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еҝ—пјҲ1983-2007пјүгҖӢеҺҶз»Ҹе…ЁеёӮ142家жүҝзј–еҚ•дҪҚгҖҒ500еӨҡеҗҚдҝ®еҝ—дәәзҡ„иү°иӢҰеҠӘеҠӣпјҢдә”и®ўзәІзӣ®пјҢе…ӯжҳ“е…¶зЁҝпјҢе…«е№ҙдҝ®и®ўпјҢжңҖз»ҲжҲҗд№Ұ200еӨҡдёҮеӯ—пјҢдәҺ2014е№ҙжӯЈејҸеҮәзүҲеҸ‘иЎҢгҖӮгҖҠй„ӮеҹҺеҢәеҝ—гҖӢгҖҠеҚҺе®№еҢәеҝ—гҖӢгҖҠжўҒеӯҗж№–еҢәеҝ—гҖӢд№ҹеҲҶеҲ«дәҺ2010е№ҙгҖҒ2015е№ҙе’Ң2016е№ҙеҮәзүҲеҸ‘иЎҢпјҢиҮіжӯӨпјҢй„Ӯе·һеёӮдёӨиҪ®дҝ®еҝ—е·ҘдҪңе…Ёйқўе®ҢжҲҗгҖӮиҝҷдёҖжңҹй—ҙпјҢд№Ўй•Үеҝ—гҖҒйғЁй—Ёеҝ—гҖҒдё“дёҡеҝ—гҖҒ姓ж°Ҹеҝ—гҖҒең°жғ…иө„ж–ҷзӯүеҲ«зұ»д№ҹйҒҚең°ејҖиҠұпјҢжҲҗжһңе–ңдәәпјҢе‘ҲзҺ°еҮәзҷҫ家дәүйёЈгҖҒзҷҫиҠұйҪҗж”ҫзҡ„з§ҜжһҒжҖҒеҠҝгҖӮ
1997е№ҙпјҢгҖҠй„Ӯе·һе№ҙйүҙгҖӢдҝ®и®ўе·ҘдҪңеҗҜеҠЁпјҢжҲҗдёәдёӨдёӘдҝ®еҝ—йҳ¶ж®өд№ӢеӨ–зҡ„еёёжҖҒжҖ§е·ҘдҪңгҖӮеңЁз¬¬дәҢиҪ®дҝ®еҝ—йҳ¶ж®өдёӯпјҢгҖҠй„Ӯе·һе№ҙйүҙгҖӢдёә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еҝ—пјҲ1983-2007пјүгҖӢжҸҗдҫӣдәҶдё°еҜҢзҡ„еҺҶеҸІиө„ж–ҷгҖӮиҮід»ҠдёәжӯўпјҢгҖҠй„Ӯе·һе№ҙйүҙгҖӢе·Іиҝһз»ӯеҮәзүҲ22йғЁгҖӮ
жҲҗжһңдё°еҜҢпјҢиҙЁйҮҸиҫҫж Ү
дёӨиҪ®дҝ®еҝ—дёӢжқҘпјҢе·Іе®ҢжҲҗзҡ„еҝ—д№ҰеҶ…е®№дё°еҜҢпјҢйҷӨдёӨйғЁ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еҝ—гҖӢгҖҒдёүдёӘеҢәеҝ—д»ҘеӨ–пјҢд№Ўй•ҮпјҲиЎ—йҒ“пјүгҖҒжқ‘еҝ—е®һзҺ°зј–дҝ®е…ЁиҰҶзӣ–пјҢйғЁй—Ёеҝ—ж¶өзӣ–йҪҗе…ЁпјҢең°жғ…иө„ж–ҷ收иҺ·дё°зЎ•пјҢе№ҙйүҙе·ҘдҪңжҢҒз»ӯиҝӣеұ•пјҢеҸӨзұҚж•ҙзҗҶеҚ“и§ҒжҲҗж•ҲгҖӮеңЁжҲҗд№ҰиҙЁйҮҸдёҠпјҢз»қеӨ§йғЁеҲҶеҝ—д№Ұиө„ж–ҷзҝ”е®һеҸҜйқ пјҢжңүе®һең°иҖғеҜҹзҡ„дёҖжүӢиө„ж–ҷпјҢдҪ“дҫӢ规иҢғпјҢиҫғй«ҳиҫҫжҲҗдәҶеҝ—д№Ұеә”жңүзҡ„ж ҮеҮҶгҖӮ
д№Ўй•ҮпјҲиЎ—йҒ“пјүгҖҒжқ‘еҝ—ж–№йқўпјҢе·ІжңүгҖҠеҮӨеҮ°иЎ—йҒ“еҝ—гҖӢгҖҠзҷҫеӯҗз•Ҳжқ‘еҝ—гҖӢзӯүеӨҡйғЁеҝ—д№ҰеҮәзүҲеҸ‘иЎҢпјӣгҖҠи‘ӣеә—ејҖеҸ‘еҢәпјҲи‘ӣеә—й•Үпјүеҝ—гҖӢе·ІжҲҗеҲқзЁҝпјӣгҖҠеҚҺе®№й•Үеҝ—гҖӢгҖҠжқңеұұжқ‘еҝ—гҖӢжӯЈеңЁзј–дҝ®гҖӮ
йғЁй—Ёеҝ—ж–№йқўпјҢе·Іе®ҢжҲҗ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з”өеҠӣеҝ—гҖӢ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ж”ҝеҚҸеҝ—гҖӢ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дәӨйҖҡиҝҗиҫ“еҝ—гҖӢзӯүиҝ‘30家еҚ•дҪҚйғЁй—Ёеҝ—пјӣ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ж•ҷиӮІеҝ—гҖӢ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ж°ҙдә§еҝ—гҖӢзӯү7йғЁеҝ—д№ҰжӯЈеңЁзј–зәӮгҖӮ
ең°жғ…иө„ж–ҷж–№йқўпјҢйҷҶз»ӯзј–зәӮеҮәзүҲдәҶгҖҠй„Ӯе·һдәәзү©гҖӢ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е»әеҲ¶жІҝйқ©еҝ—гҖӢгҖҠй„Ӯе·һж–№иЁҖеҝ—гҖӢзӯүж•°еҚҒйғЁд№ҰзұҚгҖӮ
дёәвҖңиө„жІ»гҖҒеӯҳеҸІгҖҒж•ҷеҢ–вҖқиҖҢдҝ®еҝ—
вҖңдҝ®еҝ—д»ҘиҘ„зӣӣдё–пјҢе…·жңүиө„жІ»гҖҒеӯҳеҸІгҖҒж•ҷеҢ–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вҖқеҪ“иў«й—®еҸҠдҝ®еҝ—иҰҒиҫҫеҲ°дҪ•з§Қзӣ®ж Үж—¶пјҢдҪҷдёүжҜӣиҜҙпјҢдҝ®еҝ—еңЁи®ёеӨҡдәәзңјйҮҢжҳҜдёҖйЎ№жһҜзҮҘзҡ„е·ҘдҪңпјҢдҪҶе®ғеҜ№дәҺең°ж–№еҸ‘еұ•гҖҒж–ҮеҢ–дј жүҝжңүзқҖдёҫи¶іиҪ»йҮҚ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ең°ж–№еҝ—ж—ўжҳҜеұҘж–°йўҶеҜјдәҶи§Јй„Ӯе·һзҡ„йҮҚиҰҒжқҗж–ҷпјҢд№ҹжҳҜеёӮж°‘дҪ“жӮҹй„Ӯе·һж–ҮеҢ–зҡ„йҮҚиҰҒйҖ”еҫ„пјҢиҝҳжҳҜеӯҰиҖ…иҝӣиЎҢй„Ӯе·һз ”з©¶зҡ„йҮҚиҰҒеҸӮиҖғгҖӮдёҖйғЁең°ж–№еҝ—д№ҰпјҢе°ұжҳҜдёҖйғЁең°ж–№е…ЁеҸІпјҢжҳҜзӯ‘зүўж–ҮеҢ–иҮӘдҝЎеҹәзҹізҡ„йҮҚиҰҒжүӢж®өд№ӢдёҖгҖӮ
йІҒжҹійқ’пјҡж—¶д»Јзҡ„жңүеҝғдәәеҺҶеҸІзҡ„й“ӯи®°иҖ…
в–Ўеј иғңж–ҮпјҲжӯҰжұүеӨ§еӯҰй«ҳзӯүж•ҷиӮІеӯҰзЎ•еЈ«пјү
йІҒжҹійқ’еӨ§еҚҠз”ҹйғҪеңЁдёҺж–Үеӯ—жү“дәӨйҒ“гҖӮд»–жҳҜдәәж°‘ж•ҷеёҲпјҢеңЁд№Ўжқ‘жү§ж•ҷеҮ еҚҒе№ҙпјҢжЎғжқҺж»Ўеӣӯпјӣд»–жҳҜдҪң家пјҢд»Ҙ笔дёәзҠҒпјҢд»Ҙзәёдёәз”°пјҢеҲӣдҪңеҮәи®ёеӨҡдјҳз§ҖдҪңе“Ғпјӣд»–иҝҳжҳҜдёҖеҗҚдҝ®еҝ—дәәпјҢеҚҒеҮ е№ҙжқҘпјҢжҪңеҝғз ”з©¶пјҢй»ҳй»ҳж— й—»пјҢдёәжҲ‘еёӮеҺҶеҸІж–ҮеҢ–е»әи®ҫдҪңеҮәиҙЎзҢ®гҖӮ
йІҒжҹійқ’иҮӘ2003е№ҙжҺҘи§Ұдҝ®еҝ—е·ҘдҪңпјҢжңҹй—ҙеҸӮзј–дәҶ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еҝ—гҖӢ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еҹҺ乡规еҲ’е»әи®ҫеҝ—гҖӢзӯүгҖӮз§ҜзҙҜдәҶдёҖе®ҡзҡ„дҝ®еҝ—з»ҸйӘҢеҗҺпјҢд»–ејҖе§ӢзӢ¬иҮӘзј–дҝ®еҝ—д№ҰпјҢдё»зј–дәҶ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ең°еҗҚеҝ—В·й„ӮеҹҺеҢәеҚ·гҖӢгҖҠй„ӮеҹҺеҢәең°еҗҚеҝ—гҖӢе’ҢгҖҠй„Ӯе·һйЈҺдҝ—еҝ—гҖӢгҖӮеҜ№дәҺдҝ®еҝ—иҝҷйЎ№е·ҘдҪңпјҢйІҒжҹійқ’еҚҒеҲҶи®ӨзңҹпјҢд»–и®Өдёәеҝ—д№ҰдёҚжҳҜиҜ„и®әеҺҶеҸІзҡ„д№ҰгҖҒдёҚжҳҜеҸІи®әпјҢеӨҡдҪҷзҡ„иҜ„и®әдёҚдҪҶдёҚдёәең°ж–№еҝ—еўһе…үпјҢеҸҚиҖҢиҝқиғҢдәҶеҝ—д№Ұзҡ„еҸҜдҝЎеәҰгҖӮеҘҪзҡ„ең°ж–№еҝ—пјҢеҝ…然иғҪеӨҹиҮӘи§үеқҡжҢҒзӣёе…ізҡ„зј–зәӮеҺҹеҲҷпјҢд»ҘжӯӨдҝқиҜҒеҝ—д№Ұзҡ„зңҹе®һеҸҜйқ гҖӮдҝ®еҝ—并йқһдёҖ件д№Ұж–ӢйҮҢзҡ„и‘—иҝ°е·ҘдҪңпјҢиҖҢжҳҜдёҖз§ҚеҸ‘д№ҺдәҺдё–гҖҒжңҚеҠЎдәҺдё–зҡ„еҲӣдҪңгҖӮеҸ‘д№ҺдәҺдё–пјҢжҳҜиҜҙеҝ—д№ҰеҸ–жқҗдәҺеҪ“дё–зҡ„зңҹдәӢгҖҒе®һеҶөпјҢжҺҘеҪ“дё–д№Ӣең°ж°”пјӣжңҚеҠЎдәҺдё–пјҢжҳҜиҜҙеҝ—д№Ұ并йқһзәҜзҗҶи®әд№ӢдҪңпјҢиҖҢжҳҜе®һз”Ёд№Ӣд№ҰпјҢе…¶жңҚеҠЎеҠҹиғҪе»әз«ӢеңЁеҝ—д№ҰжҸҗдҫӣзҡ„зңҹе®һиө„ж–ҷд№ӢдёҠгҖӮ
зј–еҶҷең°еҗҚеҝ—пјҢдё»иҰҒе°ұжҳҜ收еҪ•еҗ„зұ»ең°еҗҚзҡ„ж ҮеҮҶеҗҚз§°пјҢеҮҶзЎ®иЎЁиҝ°ең°еҗҚзҡ„жұүиҜӯжӢјйҹігҖҒең°зҗҶдҪҚзҪ®гҖҒеҗҚз§°жқҘеҺҶгҖҒеҗ«д№үе’Ңжј”еҸҳгҖҒеҺҶеҸІжІҝйқ©еҸҠе…¶иҮӘ然ең°зҗҶзӯүзӣёе…ідҝЎжҒҜгҖӮеңЁзј–дҝ®гҖҠй„ӮеҹҺеҢәең°еҗҚеҝ—гҖӢж—¶пјҢйІҒжҹійқ’жҹҘйҳ…дәҶеӨ§йҮҸиө„ж–ҷпјҢдҪҶжҳҜеҸҲдёҚеұҖйҷҗдәҺд№Ұжң¬пјҢд»–и®Өдёәдҝ®еҝ—дәәиҰҒеӯҰдјҡз”„еҲ«дҝЎжҒҜпјҢж•ўдәҺжҢ–жҺҳзңҹзҗҶпјҢдёҚиғҪе®Ңе…Ёз…§жҠ„д»–дәәзҡ„жқҗж–ҷпјҢиҝҷжҳҜдҝ®еҝ—е·ҘдҪңеҝ…дёҚеҸҜе°‘зҡ„дёҖз§ҚжҖҒеәҰгҖӮвҖңжұӮзңҹеӯҳе®һвҖқпјҢжҳҜиў«дҪңдёәзЎ®дҝқең°ж–№еҝ—д№ҰиҙЁйҮҸзҡ„е”ҜдёҖеүҚжҸҗеҶҷиҝӣгҖҠең°ж–№еҝ—е·ҘдҪңжқЎдҫӢгҖӢзҡ„гҖӮиҝҷжҳҜдҝ®еҝ—й—®йҒ“зҡ„дёҖдёӘдҝқйҡңпјҢжҳҜдҝ®еҝ—й—®йҒ“зҡ„дёҖз§ҚиҝҪжұӮпјҢд№ҹжҳҜдҝ®еҝ—й—®йҒ“зҡ„дёҖдёӘжҢҮеҗ‘гҖӮдәәиҖҢж— дҝЎпјҢдёҚзҹҘе…¶еҸҜпјӣеҝ—иҖҢдёҚе®һпјҢйҡҫд»ҘжҲҗеҝ—гҖӮжӯЈжүҖи°“вҖңең°иҝ‘жҳ“ж ёпјҢж—¶иҝ‘иҝ№зңҹвҖқпјҢе”Ҝе…¶зңҹе®һпјҢеҝ—д№ҰжүҚиғҪвҖңиЎҘеҸІд№ӢзјәпјҢеҸӮеҸІд№Ӣй”ҷпјҢиҜҰеҸІд№Ӣз•ҘпјҢз»ӯеҸІд№Ӣж— вҖқгҖӮжҜ”еҰӮе…ідәҺй„Ӯе·һд№ӢеүҚдёәдҪ•иў«з§°дёәвҖңжӯҰжҳҢвҖқпјҢе°ұжңүдёҚеҗҢзҡ„иҜҙжі•гҖӮжңүдәәи®ӨдёәеҪ“ж—¶жңүдёӘвҖңжӯҰжҳҢеұұвҖқпјҢжүҖд»ҘжӯӨең°иў«е‘ҪеҗҚдёәвҖңжӯҰжҳҢвҖқпјҢдҪҶжҳҜеңЁйҷҲеҜҝзҡ„гҖҠдёүеӣҪеҝ—гҖӢдёӯеҲҷиҜҙпјҢеҪ“ж—¶еӯҷжқғиҝҒиҮій„ӮеҺҝпјҢе‘ҪеҗҚдёәвҖңжӯҰжҳҢвҖқпјҢжҳҜдёәдәҶи®©зҷҫ姓е’ҢеЈ«е…өеұ…е®үжҖқеҚұпјҢж—¶еҲ»дҝқжҢҒиӯҰжғ•пјҢд»ҘжӯҰиҖҢжҳҢпјҢеңЁеӨӘе№іе№ҙд»Јд№ҹдёҚеҝҳжӯҰеҠӣзҡ„йҮҚиҰҒжҖ§гҖӮд»ҺиҝҷйҮҢеҸҜд»ҘзңӢеҮәпјҢиҰҒз”„еҲ«дёҖдёӘй—®йўҳзҡ„зңҹе®һжҖ§пјҢйңҖиҰҒжҹҘйҳ…иө„ж–ҷпјҢеӨҡж–№дҪҗиҜҒпјҢз»қдёҚеҸҜдәәдә‘дәҰдә‘гҖӮең°еҗҚеҝ—жңүе…¶зү№ж®Ҡзҡ„ж„Ҹд№үпјҢйІҒжҹійқ’и®Өдёәең°еҗҚеҝ—и®°еҪ•дәҶдёҖдёӘең°ж–№еҸ‘еұ•зҡ„еҺҶеҸІиҪЁиҝ№пјҢ延з»ӯдәҶеҺҶеҸІзҡ„ж–Үи„үпјҢжңүеҠ©дәҺдәә们дәҶи§Је…¶дә§з”ҹдёҺеҸ‘еұ•зҡ„еҺҶеҸІжІҝйқ©е’Ңең°еҗҚжүҖи•ҙеҗ«зҡ„ж–ҮеҢ–еҶ…ж¶өпјҢе…·жңүеҫҲй«ҳзҡ„еӯҰжңҜд»·еҖје’ҢеӯҳеҸІд»·еҖјгҖӮ
жҘјйҳҙгҖҠйЈҺдҝ—зәӘзәІгҖӢжӣ°пјҡвҖңеӣҪ家д№Ӣе…ғж°”пјҢе…ЁеңЁйЈҺдҝ—гҖӮйЈҺдҝ—д№Ӣжң¬пјҢе®һзі»зәІзәӘгҖӮвҖқйЈҺдҝ—жҳҜд»ҺеҸӨиҮід»ҠдёҖзӣҙдј жүҝжІҝиўӯзҡ„пјҢжҳҜ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дј з»ҹж–ҮеҢ–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йІҒжҹійқ’е…Ҳз”ҹеңЁеӨҡе№ҙзҡ„е·ҘдҪңдёӯйҖҗжёҗж„ҸиҜҶеҲ°йЈҺдҝ—еҜ№дәҺдёҖдёӘең°еҢәзҡ„йҮҚиҰҒж„Ҹд№үпјҢдәҺжҳҜдә§з”ҹзј–зәӮгҖҠй„Ӯе·һйЈҺдҝ—еҝ—гҖӢзҡ„жғіжі•гҖӮгҖҠй„Ӯе·һйЈҺдҝ—еҝ—гҖӢиҷҪ然еҸҚжҳ зҡ„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ең°еҢәзҡ„йЈҺеңҹдәәжғ…пјҢеҚҙиө·еҲ°зӘҘдёҖж–‘иҖҢзҹҘе…Ёиұ№зҡ„дҪңз”ЁпјҢи®©дәә们зҹҘдҝ—гҖҒе°ҠзӨјгҖҒе®Ҳжі•пјҢеўһејәж°‘ж—ҸиҮӘдҝЎеҝғе’ҢиҮӘиұӘж„ҹгҖӮ
дёәдәҶзј–зәӮиҝҷжң¬йЈҺдҝ—еҝ—пјҢйІҒжҹійқ’иҠұиҙ№дәҶдёҚе°‘зІҫеҠӣе’ҢеҝғиЎҖпјҢд»–еҸӮйҳ…дәҶгҖҠдёӯеӣҪйЈҺдҝ—еҸІгҖӢгҖҒе…үз»ӘгҖҠжӯҰжҳҢеҺҝеҝ—гҖӢгҖҠй„Ӯе·һеёӮеҝ—гҖӢгҖҠй„ӮеҹҺеҢәеҝ—гҖӢгҖҠеҚҺе®№еҢәеҝ—гҖӢгҖҠжўҒеӯҗж№–еҢәеҝ—гҖӢзӯүеҝ—д№ҰеҸҠеҚҒеҮ йғЁжқ‘еҝ—пјҢиө„ж–ҷеәһжқӮпјҢе·ҘдҪңйҮҸе·ЁеӨ§гҖӮеңЁдҝ®еҝ—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»–е§Ӣз»Ҳз§үжҢҒвҖңжұӮзңҹеӯҳе®һвҖқеҺҹеҲҷгҖӮйЈҺдҝ—еҝ—иҫғдёәзү№ж®ҠпјҢиҰҒжғідәҶи§ЈеҪ“ең°йЈҺдҝ—пјҢе…үзңӢиө„ж–ҷжҳҜдёҚеӨҹзҡ„пјҢеҝ…йЎ»е®һең°иө°и®ҝгҖӮйІҒжҹійқ’з”ЁдәҶ5е№ҙеӨҡж—¶й—ҙпјҢи·‘йҒҚе…ЁеёӮ3дёӘеҢәзҡ„ж•°зҷҫдёӘжқ‘ж№ҫпјҢжӢңи®ҝиҝҮж•°д»Ҙзҷҫи®Ўзҡ„жқ‘е№ІйғЁгҖҒиҖҒеҶңгҖҒе·ҘеҢ гҖҒж°‘й—ҙиүәдәәгҖҒж°‘й—ҙеҺҶеҸІж–ҮеҢ–з ”з©¶иҖ…е’ҢеҹҺй•ҮеҚҡеӯҰиҜҶе№ҝдәәеЈ«гҖӮиҝҷж®өж—¶й—ҙйҮҢпјҢйІҒжҹійқ’дёҚжҳҜиЎҢиө°еңЁи·ҜдёҠпјҢе°ұжҳҜз§үзғӣжЎҢеүҚпјҢжңүж—¶дёӢд№Ўиө°и®ҝпјҢиҝҳдјҡиў«дәәеҪ“жҲҗйӘ—еӯҗпјҢе…¶дёӯеҝғй…ёдёҚдёҖиҖҢи¶ігҖӮ
еҘҪеңЁйІҒжҹійқ’еӨ©жҖ§д№җи§ӮгҖҒеқҡйҹ§пјҢ他并дёҚи®ӨдёәжҹҘйҳ…иө„ж–ҷжҳҜ件жһҜзҮҘ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жҜҸдёҖж¬Ўйҳ…иҜ»йғҪиғҪи®©иҮӘе·ұзҡ„зҹҘиҜҶе®қеә“жӣҙеҠ дё°еҜҢпјӣдёӢд№ЎйҮҮи®ҝпјҢд»–д№ҹдёҚи®ӨдёәжҳҜ件йә»зғҰдәӢпјҢжҜҸдёҖж¬ЎеҮәиЎҢйғҪдёәиҮӘе·ұзҡ„е°ҸиҜҙеҲӣдҪңеўһж·»дәҶзҒөж„ҹпјӣиў«йҮҮи®ҝеҜ№иұЎиҜҜи§ЈпјҢд»–д№ҹ并дёҚзҒ°еҝғпјҢеҸҚиҖҢжҖ»з»“еҮәдёҖеҘ—йҮҮи®ҝжҠҖе·§пјҢжҙ»еӯҰжҙ»з”ЁгҖӮйІҒжҹійқ’д№ӢжүҖд»Ҙж„ҝж„Ҹеҗғиҝҷд№ҲеӨҡиӢҰпјҢи·‘иҝҷд№ҲеӨҡи·ҜпјҢеҪ’ж №з»“еә•пјҢиҝҳжҳҜжәҗдәҺд»–еҜ№дҝ®еҝ—е·ҘдҪңзҡ„зғӯзҲұпјҢжғіеҲ°иғҪеӨҹжҠҠй„Ӯе·һдј з»ҹд№ дҝ—з”Ёж–Үеӯ—и®°еҪ•дёӢжқҘпјҢи®©й„Ӯе·һж–ҮеҢ–дј жүҝпјҢиҖҒе…Ҳз”ҹеҝғйҮҢе°ұи§үеҫ—еҖјгҖӮдҝ®еҝ—еҚідҝ®еҝғпјҢйІҒжҹійқ’дёҚдёәеҗҚпјҢдёҚдёәеҲ©пјҢе§Ӣз»ҲдҝқжҢҒзқҖвҖңдҝ®еҝ—й—®йҒ“пјҢд»ҘеҗҜжңӘжқҘвҖқзҡ„еҲқеҝғпјҢи·өиЎҢзқҖдј жүҝдёӯеҚҺж–ҮжҳҺгҖҒеҸ‘жҺҳеҺҶеҸІжҷәж…§зҡ„иҙЈд»»жӢ…еҪ“гҖӮ
еј е…Ҳиғңпјҡеӣ дёәзғӯзҲұжүҖд»ҘеүҚиЎҢ
в–ЎзЁӢй№ғпјҲжӯҰжұүеӨ§еӯҰиЎҢж”ҝз®ЎзҗҶзЎ•еЈ«пјү
еј е…Ҳиғңе…Ҳз”ҹжҳҜдёҖдҪҚжңүжғ…жҖҖгҖҒжңүжӢ…еҪ“зҡ„ж–ҮеҢ–дәәгҖӮ
2008е№ҙиҮі2014е№ҙй—ҙпјҢд»–еҸӮдёҺдәҶжўҒеӯҗж№–еҢәж”ҝеәңдё»жҢҒзј–дҝ®зҡ„гҖҠжўҒеӯҗж№–еҢәеҝ—гҖӢзҡ„зј–зәӮе·ҘдҪңпјҢ任主笔гҖӮиҜҘд№ҰдәҺ2016е№ҙеҮәзүҲпјҢеҶ…е®№ж¶үеҸҠжўҒеӯҗж№–еҢәиҮӘ然гҖҒз»ҸжөҺгҖҒж”ҝжІ»гҖҒж–ҮеҢ–е’ҢзӨҫдјҡзӯүеҗ„дёӘж–№йқўпјҢе…ұ13зҜҮ80дҪҷдёҮеӯ—пјҢиҝҗз”Ёиҝ°гҖҒи®°гҖҒеҝ—гҖҒдј гҖҒеӣҫгҖҒиЎЁгҖҒеҪ•зӯүеҪўејҸпјҢи®°иҝ°дәҶжўҒеӯҗж№–ең°еҢәдёҠиҮӘе‘ЁеӨ·зҺӢдёғе№ҙпјҲе…¬е…ғеүҚ879е№ҙпјүпјҢдёӢиҮі2005е№ҙ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1987е№ҙе»әеҢәд»ҘжқҘзҡ„еҺҶеҸІйқўиІҢе’Ңе·ЁеӨ§еҸҳеҢ–пјҢдҪ“дҫӢе®ҢеӨҮпјҢиө„ж–ҷзҝ”е®һпјҢеҲҶзұ»еҫ—еҪ“пјҢзј–жҺ’еҗҲзҗҶпјҢиҜӯиЁҖз®ҖжҙҒжөҒз•…гҖҒзңҹе®һе®ўи§ӮпјҢиў«иӘүдёәжўҒеӯҗж№–еҢәвҖң第дёҖзҷҫ科全д№ҰвҖқгҖӮ
еј е…ҲиғңиҜҙпјҢеңЁзј–зәӮгҖҠжўҒеӯҗж№–еҢәеҝ—гҖӢзҡ„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»–е’ҢеҗҢдәӢ们收еҪ•дәҶеҮ зҷҫдёҮеӯ—зҡ„еҺҹе§Ӣиө„ж–ҷпјҢ然еҗҺиҝӣиЎҢж•ҙзҗҶгҖҒз”„еҲ«е’ҢжұӮиҜҒпјҢдёҚеҲҶеҜ’жҡ‘гҖҒдёҚи®ЎжҳјеӨңпјҢи¶іиҝ№йҒҚеҸҠжўҒеӯҗж№–еҢәеҸҠзӣёйӮ»зҡ„еӨ§еҶ¶гҖҒжӯҰжұүеёӮжӯҰжҳҢеҢәзӯүең°гҖӮ
й—®иө·дёәд»Җд№ҲиҰҒд»ҺдәӢдҝ®еҝ—е·ҘдҪңж—¶пјҢеј е…ҲиғңдёҚеҒҮжҖқзҙўең°иҜҙпјҡвҖңеӣ дёәзғӯзҲұпјҒвҖқиҝҷзҲұеҢ…жӢ¬2дёӘж–№йқўпјҡдҪңдёәеңҹз”ҹеңҹй•ҝзҡ„жўҒеӯҗж№–дәәпјҢд»–ж·ұж·ұзҲұзқҖи„ҡдёӢиҝҷзүҮеңҹең°пјӣеҜ№зҘ–еӣҪж–Үеӯ—е’Ңж–ҮеҢ–зҡ„зғӯзҲұгҖӮдёҠдё–зәӘ80е№ҙд»ЈеҲқпјҢеј е…Ҳиғңй«ҳиҖғеӨұеҲ©пјҢеӣһжқ‘е°ҸеӯҰеҒҡдәҶдёҖеҗҚж°‘еҠһж•ҷеёҲпјҢдёҖеҫ…е°ұжҳҜ6е№ҙгҖӮйӮЈжҳҜдёӘеҒҸеғ»зҡ„еұұжқ‘пјҢжқЎд»¶еҫҲиү°иӢҰпјҢжІЎжңүд»Җд№ҲдёҡдҪҷж–ҮеҢ–з”ҹжҙ»гҖӮ然иҖҢпјҢеј е…ҲиғңеҲ©з”Ёиҝҷ6е№ҙж—¶й—ҙпјҢйҳ…иҜ»дәҶеӨ§йҮҸе“ІеӯҰгҖҒж–ҮеӯҰе’ҢеҸІеӯҰд№ҰзұҚпјҢе…»жҲҗдәҶиүҜеҘҪзҡ„йҳ…иҜ»д№ жғҜе’ҢеҶҷдҪңд№ жғҜгҖӮеңЁд»ҘеҗҺзҡ„еІҒжңҲйҮҢпјҢд»–жҜҸеӨ©еқҡжҢҒйҳ…иҜ»пјҢз”ҡиҮіеңЁжӯҰжұүеҗҢжөҺеҢ»йҷўеҒҡеҷЁе®ҳ移жӨҚжүӢжңҜжңҹй—ҙпјҢиҝҳ让家дәәд№°жқҘгҖҠе°јйҮҮзҡ„з”ҹеӯҳе“ІеӯҰгҖӢпјҢжҜҸеӨ©зңӢеҮ йЎөгҖӮ
2008е№ҙпјҢеј е…Ҳиғңиә«жӮЈйҮҚз–ҫпјҢж— еҠӣз«ҷеңЁи®ІеҸ°дёҠиҜҫпјҢдҪҶд»–дёҚз”ҳдәҺеқҗеҗғзӯүжӯ»пјҢиҝҳжҳҜеҮҶеӨҮиҫ№жІ»з—…иҫ№еҒҡзӮ№еҠӣжүҖиғҪеҸҠзҡ„е·ҘдҪңгҖӮеҗ¬иҜҙжўҒеӯҗж№–еҢәж”ҝеәңжӯЈеңЁзү©иүІдәәе‘ҳзј–дҝ®еҢәеҝ—пјҢд»–иҮӘе‘ҠеҘӢеӢҮи·‘еҲ°еҢәж”ҝеәңеҠһе…¬е®ӨпјҢжүҫеҲ°жңүе…ійўҶеҜјпјҢиҰҒжұӮжүҝжӢ…еҢәеҝ—зҡ„зј–зәӮе·ҘдҪңпјҢжү§з¬”дёә家乡дҝ®еҝ—гҖӮ
然иҖҢпјҢ他并没жңүж–ҷеҲ°дҝ®еҝ—е·ҘдҪңжһҒе…¶иү°иӢҰпјҢдјҡж¶үеҸҠзӨҫдјҡзҡ„еҗ„дёӘйғЁй—ЁгҖҒж–№ж–№йқўйқўпјҢж¶үеҸҠи®ёеӨҡзҹҘиҜҶйўҶеҹҹпјҢеҮ д№ҺиҰҒжұӮдҝ®еҝ—иҖ…жҲҗдёәзҷҫ科全д№ҰејҸзҡ„дәә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йҡҸзқҖж—¶й—ҙжҺЁз§»пјҢеј е…Ҳиғңзҡ„иә«дҪ“зҠ¶еҶөи¶ҠжқҘи¶Ҡе·®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д»–жІЎжңүеҗ‘з—…йӯ”еұҲжңҚпјҢеқҡжҢҒдёҖиҫ№е°ұеҢ»дёҖиҫ№з»§з»ӯзј–еҶҷеҢәеҝ—гҖӮеҝ—д№Ұзҡ„зј–зәӮжҳҜдёҖ件йқһеёёдёҘи°Ёзҡ„е·ҘдҪңпјҢе®№дёҚеҫ—еҚҠзӮ№й©¬иҷҺпјҢеј е…ҲиғңеҝҚзқҖз—…з—ӣпјҢе’¬зүҷеқҡжҢҒеҘ”жіўдәҺеҗ„дёӘеҚ•дҪҚд№Ӣй—ҙ收йӣҶиө„ж–ҷгҖҒеӨҡеӨ„жұӮиҜҒпјҢз»Ҳж—ҘеҝҷзўҢдәҺжЎҲзүҚд№ӢдёҠпјҢеҜ№ж•ҙзҗҶеҮәжқҘзҡ„ж–Үеӯ—иҝӣиЎҢеҸҚеӨҚж ЎеҜ№гҖҒжұӮзңҹжұӮе®һгҖҒеқҡе®Ҳжң¬еҝғпјҢдёҖе№Іе°ұжҳҜ5е№ҙгҖӮжңүдёҖж¬ЎпјҢеј е…ҲиғңеңЁе’ҢзңҒгҖҒеёӮ专家дәӨи°ҲдёӯиҺ·жӮүпјҢж°‘еӣҪж—¶дёңжІҹжңҲеұұдәәжқЁдёңжқҘе…Ҳз”ҹзј–дәҶдёҖйғЁгҖҠжңҲеұұжқ‘еҝ—гҖӢпјҢеҺҹзЁҝ被收и—ҸеңЁеӣҪ家еӣҫд№ҰйҰҶгҖӮеӣ еҝ—д№Ұдёӯжқ‘еҝ—еӯҳйҮҸдёҚеӨҡпјҢеҸҲжҳҜжүӢеҶҷеӯӨжң¬пјҢдё”гҖҠжңҲеұұжқ‘еҝ—гҖӢеңЁдҪ“дҫӢдёҠжңүеҲӣж–°пјҢеҫҲжңүеӯҰжңҜд»·еҖјпјҢд»–еҶіеҝғе°ҶиҜҘжқ‘еҝ—иҫ‘е…ҘгҖҠжўҒеӯҗж№–еҢәеҝ—гҖӢзҡ„йҷ„еҪ•дёӯгҖӮз»ҸиҝҮеӨҡж–№жү“еҗ¬пјҢеј е…ҲиғңиҺ·зҹҘжңҲеұұжқ‘жңүдәәеҮәзүҲдёҖйғЁгҖҠжңҲеұұжҳҘз§ӢгҖӢпјҢиҜҘд№Ұе…Ёж–Үеј•з”ЁдәҶжқЁдёңжқҘе…Ҳз”ҹзҡ„гҖҠжңҲеұұжқ‘еҝ—гҖӢпјҢд»–дҫҝйӘ‘зқҖж‘©жүҳиҪҰпјҢе…ҲеҗҺ2ж¬ЎеүҚеҫҖжңҲеұұжқ‘пјҢз»ҲдәҺиҺ·еҫ—иҜҘд№ҰпјҢиҝһеӨңеҪ•е…ҘпјҢ第дәҢеӨ©еҶҚйӘ‘иҪҰеҺ»йҖҒиҝҳгҖӮдҝ®еҝ—иҝҮзЁӢдёӯдјҡйҒҮеҲ°и®ёеӨҡдёҚжҮӮзҡ„дёңиҘҝпјҢд»–е°ұиҫ№зңӢиҫ№и®°гҖҒиҫ№й—®иҫ№еӯҰпјҢеҗ‘зңҒгҖҒеёӮ专家жұӮж•ҷпјҢеҗ‘еҗҢиЎҢжұӮж•ҷпјҢеҗ‘еҗ„иЎҢеҗ„дёҡзҡ„иҫҫдәәжұӮж•ҷгҖӮиә«дҪ“жҜҸеҶөж„ҲдёӢпјҢд»–е°ұзҷҪеӨ©й»‘еӨңеҠ зҸӯеҶҷдҪңпјҢеёҢжңӣиғҪе°Ҫеҝ«е®ҢжҲҗгҖӮ2013е№ҙеә•пјҢгҖҠжўҒеӯҗж№–еҢәеҝ—гҖӢйҖҡиҝҮдәҢе®ЎпјҢжҸҗиҜ·зңҒеҸІеҝ—еҠһйўҶеҜје’Ң专家з»Ҳе®ЎгҖӮиҝҷж—¶зҡ„еј е…Ҳиғңе·Із»Ҹз—…еҫ—дёҚиғҪиө·еәҠпјҢдёҚеҫ—дёҚдҪҸйҷўжҺҘеҸ—жІ»з–—гҖӮ
еј е…ҲиғңдёҚеҝҳеҲқеҝғпјҢеҠӘеҠӣдёәзӨҫдјҡдҪңиҙЎзҢ®пјҢзӨҫдјҡд№ҹжІЎжңүеҝҪи§Ҷд»–зҡ„з—…з—ӣгҖӮеҪ“еј е…Ҳиғңеӣ дёәе·ЁйўқжүӢжңҜиҙ№дёҖзӯ№иҺ«еұ•ж—¶пјҢй„Ӯе·һзҡ„ж–ҮеҸӢ们еҫ—зҹҘж¶ҲжҒҜпјҢзә·зә·ж…·ж…Ёи§ЈеӣҠпјҢ并дёәе…¶еҸ‘ж–Үзӯ№ж¬ҫгҖӮеңЁеёӮйўҶеҜјзҡ„е…іжҖҖдёӢпјҢзӨҫдјҡеҗ„з•Ңзә·зә·дјёеҮәжҸҙжүӢпјҢеј е…Ҳиғңзҡ„з—…еҫ—д»ҘжҲҗеҠҹжІ»з–—гҖӮ
еӣһжғіиҝҷж®өз»ҸеҺҶпјҢд»Өдәәе”ҸеҳҳдёҚе·ІпјҢдҪҶеј е…ҲиғңеҚҙеҫҲж¬Јж…°пјҢ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йӮЈдёӘж—¶еҖҷжё…жҘҡең°зҹҘйҒ“з–ҫз—…йҡҸж—¶дјҡеӨәиө°жҲ‘зҡ„з”ҹе‘ҪпјҢдҪҶжҳҜжҲ‘еҸӘжғіеңЁжңүз”ҹд№Ӣе№ҙе°Ҫеҝ«жҠҠеҸІеҝ—зј–еҘҪпјҢиҝҷжүҚеҜ№еҫ—иө·з”ҹжҲ‘е…»жҲ‘зҡ„жўҒеӯҗж№–пјҢеҜ№еҫ—иө·иҮӘе·ұзҡ„з”ҹе‘ҪгҖӮвҖқеҰӮд»ҠеҶҚи°Ҳиө·дҝ®еҝ—пјҢеј е…Ҳиғңж„ҹжӮҹиүҜеӨҡпјҡвҖңдҝ®еҝ—е’Ңж–ҮеӯҰеҲӣдҪңжҳҜзӣёйҖҡзҡ„пјҢйғҪеҜ№ж–ҮеӯҰзҙ е…»жңүзқҖеҫҲй«ҳиҰҒжұӮпјҢдҪҶеҸҲжҳҜдёҚеҗҢзҡ„пјҢдҝ®еҝ—зҡ„иҜӯиЁҖ讲究з®ҖжҙҒеҮҶзЎ®пјҢдёҚиҰҒдҝ®йҘ°пјҢжӣҙеғҸеҒҡдәәзҡ„йҒ“зҗҶ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жҲ‘们иҰҒжҙ»еҲ°иҖҒпјҢеӯҰеҲ°иҖҒпјҢиҝҷж ·жүҚиғҪдёҚж–ӯжҲҗй•ҝгҖӮвҖқ
зҶҠеҜҝжҳҢпјҡйҒҚеҜ»еҚҡзү©з§ү笔зӣҙд№Ұ
в–ЎзӣӣжұҹеҚ—пјҲжӯҰжұүеӨ§еӯҰеӣҫд№Ұжғ…жҠҘеӯҰзЎ•еЈ«пјү
вҖңеӣӣеӣҙеұұжӢұзҝ пјҢи„үи„үеҮәзҒөжіүвҖқгҖӮ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жҳҜдҪӣж•ҷеҮҖеңҹе®—зҡ„иө·жәҗпјҢд№ҹжҳҜе®Ӣд»ЈеҗҚеЈ«иӢҸиҪјй’ҹзҲұд№Ӣең°пјҢиҮӘдёңжҷӢд»ҘжқҘпјҢеҺҶз»Ҹе…ӯжҜҒдёғе»әпјҢеҚҙдҫқ然еІҝ然дәҺиҘҝеұұд№ӢдёҠпјҢеәҮжҠӨдёҖж–№гҖӮвҖңд»ҺеҺҶеҸІең°дҪҚжқҘиҜҙпјҢ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жӢҘжңүж·ұеҺҡзҡ„еҺҶеҸІж–ҮеҢ–еә•и•ҙпјҢдёҚд»…жҳҜй„Ӯе·һпјҢз”ҡиҮіжҳҜж№–еҢ—зңҒе®—ж•ҷж–ҮеҢ–е’ҢеҺҶеҸІж–ҮеҢ–зҡ„йӣҶдёӯеұ•зӨәең°пјӣд»ҺзӨҫдјҡйңҖжұӮжқҘиҜҙпјҢ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дёҖзӣҙзјәе°‘дёҖжң¬зі»з»ҹе®ҢеӨҮзҡ„еҜәеәҷдё“еҝ—пјҢй„Ӯе·һең°ж–№еҸІеҝ—йғЁй—Ёд№ҹеҜ№жӯӨеҝ—дҝ®и‘—з»ҷдәҲдәҶеӨ§еҠӣж”ҜжҢҒгҖӮвҖқиҒҠеҲ°дҝ®еҝ—зҡ„еҺҹеӣ пјҢеёӮеҚҡзү©йҰҶж–Үзү©дё“家зҶҠеҜҝжҳҢе…Ҳз”ҹеҰӮжҳҜиҜҙгҖӮ
вҖңжҲ‘жң¬дәәжҳҜдёҖдёӘж–Үзү©е·ҘдҪңиҖ…пјҢиҝҷд№ҹжҳҜжҲ‘第дёҖж¬Ўдҝ®и‘—ең°ж–№еҸІеҝ—пјҢеҜ№иҝҷйЎ№е·ҘдҪңдёқжҜ«дёҚж•ўжҮҲжҖ гҖӮвҖқзҶҠеҜҝжҳҢд»Һд№ҰжҹңйҮҢжӢҝеҮәдёҖжң¬гҖҠ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еҝ—гҖӢйҖ’з»ҷжҲ‘пјҢжіӣй»„зҡ„зәёеј жІүж·ҖдәҶеҸӨеҜә1600дҪҷе№ҙзҡ„йЈҺйӣЁжІ§жЎ‘гҖӮжҲ‘жҺҘиҝҮд№Ұд»”з»Ҷзҝ»зңӢпјҢе…Ҳз”ҹдҝ®еҝ—ж—¶зҡ„е…үжҷҜд№ҹйҖҗжёҗеңЁи„‘жө·йҮҢжө®зҺ°еҮәжқҘгҖӮ
еҰӮеҗҢзҶҠеҜҝжҳҢеңЁгҖҠ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еҝ—гҖӢзҡ„еҗҺи®°дёӯжүҖеҶҷпјҢзј–зәӮгҖҠ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еҝ—гҖӢжҳҜдёҖж¬ЎвҖңзҘһеңЈиҖҢеҸҲиү°йҡҫз”ҡиҮійҡҫд»ҘйҖҫи¶Ҡзҡ„жҢ‘жҲҳвҖқгҖӮеңЁеүҚжңҹеҺҶеҸІиө„ж–ҷзҡ„收йӣҶ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зҶҠеҜҝжҳҢе°ұйҒҮеҲ°дәҶйҡҫйўҳпјҢиҮӘж…§иҝңзҘ–еёҲе»әеҜәд»ҘжқҘпјҢеҜәеәҷ规模дёҚж–ӯжү©еӨ§пјҢеҸҜеҜәйҷўе»әзӯ‘еұЎйҒӯжҚҹжҜҒпјҢеҺҶеҸІжЎЈжЎҲиҚЎз„¶ж— еӯҳпјҢи„үз»ңжІҝйқ©дёҘйҮҚзјәеӨұпјҢеҚ—еҢ—жңқгҖҒйҡӢгҖҒе”җгҖҒе…ғеҺҶеҸІиө„ж–ҷеҮ д№Һз©әзҷҪгҖӮ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д»ҘжқҘпјҢе…ҡе’ҢеӣҪ家иҗҪе®һдәҶе®—ж•ҷж”ҝзӯ–пјҢеҜәеәҷз®ЎзҗҶж—Ҙи¶Ӣе®Ңе–„пјҢз”ұдәҺеғ§дәәзҡ„ж–ҮеҢ–зҙ иҙЁжңүйҷҗпјҢжЎЈжЎҲз®ЎзҗҶе·ҘдҪң并дёҚ规иҢғпјҢж— еҪўдёӯз»ҷеҜәеҝ—зј–зәӮе·ҘдҪңеёҰжқҘдәҶе·ЁеӨ§еӣ°йҡҫгҖӮ
вҖңеҶҚйҡҫд№ҹиҰҒжҗһеҮәжқҘгҖӮвҖқзҶҠеҜҝжҳҢж–©й’үжҲӘй“Ғең°иҜҙгҖӮеҜәеҝ—зј–зәӮеүҚжңҹпјҢиғЎиҢӮж–°е…Ҳз”ҹе°ұжӢҝеҮәдәҶзј–зәӮжҖ»зәІпјҢдҪҶеңЁе…·дҪ“зј–зәӮ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еёёеҮәзҺ°еӣ еҺҶеҸІиө„ж–ҷзјәеӨұиҖҢж— жі•ж”Ҝж’‘жҹҗдёӘз« иҠӮи®°иҝ°зҡ„еӣ°еўғпјҢеҶҷдҪңзҸӯеӯҗеҸӘеҘҪе°ҶжҖ»зәІдёҖеҶҚдҝ®ж”№пјҢд»ҘжңҹжңҖеӨ§йҷҗеәҰе®Ңе–„еҜәеҝ—зҡ„дҪ“дҫӢе’Ңз»“жһ„гҖӮеҘҪеңЁ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дҪңдёәеҺҶд»ЈйҮҚзӮ№еҜәйҷўпјҢжңүзқҖ1600дҪҷе№ҙдҪӣж•ҷдј жүҝзҡ„еҚ°и®°пјҢжңүи®ёеӨҡи®°иҪҪдёҚеҗҢзЁӢеәҰеҲҶж•ЈеңЁең°ж–№еҝ—е’Ңж°‘й—ҙи‘—иҝ°д№ӢдёӯпјҢеҸҜд»Ҙдёәзј–зәӮе·ҘдҪңжҸҗдҫӣдёҖе®ҡзҡ„е®һиҜҒе’ҢеҸӮиҖғгҖӮд№ҹжӯЈжҳҜеӣ дёәиҝҷдёӘеҺҹеӣ пјҢзҶҠеҜҝжҳҢдёәдәҶзӯӣйҖүз”„еҲ«иҝҷдәӣе…ёзұҚдёӯзҡ„й”ҷи®№дёҺзҹӣзӣҫд№ӢеӨ„пјҢиҝҳеҺҹдёҖдёӘзңҹе®һе®ўи§Ӯзҡ„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пјҢејҖе§ӢдәҶдёәжңҹ3е№ҙзҡ„еҝҷзўҢдёҺеҘ”жіўгҖӮ
еңЁиҝҷ3е№ҙй—ҙпјҢеҸӘиҰҒеҗ¬еҲ°дёҺеҸӨеҜәзӣёе…ізҡ„еҸІж–ҷпјҢи·ҜйҖ”еҶҚиҝңпјҢзҶҠеҜҝжҳҢйғҪиҰҒеҺ»пјҢиҷҪ然常常жҳҜд№ҳе…ҙиҖҢеҺ»пјҢиҙҘе…ҙиҖҢеҪ’пјҢдҪҶд»–д»ҚдёҚиӮҜж”ҫиҝҮдёҖдёқдёҖжҜ«зәҝзҙўгҖӮз»ҸиҝҮеӨҡж¬Ўе®һең°иҖғеҜҹгҖҒзҺ°еңәи®ҝи°ҲпјҢеҜәеҝ—зјәеӨұйғЁеҲҶд№ҹдёҖзӮ№зӮ№зҝ”е®һиө·жқҘгҖӮиҖғеҜҹд№ӢдҪҷпјҢд»–зЁҚжңүз©әй—Іе°ұеёҰзқҖе„ҝеӯҗеҫҖ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еҺ»пјҢдёҺеҜәеәҷеғ§дәәеҗҢеҗғдҪҸпјҢд»Һз»Ҹж–Үж•°йҮҸеҲ°дәәе‘ҳжһ„жҲҗпјҢеҶҚеҲ°е»әзӯ‘з»“жһ„гҖҒж®ҝе ӮеёғеұҖпјҢ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зҡ„дёҖиҚүдёҖжңЁд»–йғҪдәҶеҰӮжҢҮжҺҢгҖӮвҖңжҲ‘иҝҷйҮҢиҝҳдҝқеӯҳзқҖйӮЈдёӘж—¶еҖҷжӢҚзҡ„з…§зүҮгҖӮвҖқд»–жӢҝеҮәдёҖйғЁиҖҒејҸзӣёжңәз»ҷжҲ‘зңӢпјҢж•°еҚғеј жҸҸз»ҳеҸӨеҜәеҺҶеҸІйЈҺзү©е’Ңеғ§дҫЈз”ҹжҙ»еӣҫжҷҜзҡ„зӣёзүҮпјҢдёҖдёӢеӯҗе°ҶжҲ‘еёҰеҲ°дәҶйӮЈдёӘжҷЁй’ҹжҡ®йј“гҖҒзғӣз…§йҰҷи–°зҡ„дё–з•ҢйҮҢгҖӮеҜ№дәҺе…¶дёӯз№ҒеӨҡзҡ„зў‘жӢ“зӣёзүҮпјҢжҲ‘жңүдәӣдёҚи§ЈпјҢд»–и§ЈйҮҠиҜҙпјҡвҖңзў‘ж–Үе№ҙд»Јд№…иҝңпјҢеӯ—иҝ№жЁЎзіҠйҡҫиҫЁпјҢзӣёжңәзӣҙжӢҚйҡҫеәҰеҫҲеӨ§пјҢжүҖд»ҘжҲ‘们е°ҶеҜәйҮҢзҡ„жҜҸдёҖеқ—зў‘ж–ҮйғҪеҒҡдәҶжӢ“еҚ°пјҢжӢҚз…§д№ӢеҗҺиҝҳиҰҒ用笔жҠ„еҪ•гҖӮвҖқзңӢдјјз®ҖеҚ•зҡ„жӯҘйӘӨпјҢеҚҙеўһеҠ дәҶжҲҗеҖҚзҡ„е·ҘдҪңйҮҸгҖӮд№ҹжӯЈжҳҜиҝҷз§ҚдёҘи°Ёз»ҶиҮҙзҡ„е·ҘдҪңжҖҒеәҰпјҢдҪҝд»–жңүдәҶеүҚдәәжңӘжңүзҡ„еҸ‘зҺ°гҖӮеҸӨеҜәи—Ҹз»ҸжҘјйҡҗи”ҪеӨ„зҡ„дёҖеә§ж®Ӣзў‘дёҠпјҢеҲ»зқҖжё…е’ёдё°е№ҙй—ҙйҮҚиҮЈжӣҫеӣҪи—©зҡ„гҖҠи®ЁиҙјжӘ„гҖӢпјҢжӯӨзў‘дёәйӮ‘дәәзҺӢ家璧е“Қеә”жӣҫеӣҪи—©еҜ№еӨӘе№іеҶӣзҡ„и®ЁдјҗиҖҢеҲ»еҲ¶пјҢеӣ е№ҙд»Јд№…иҝңпјҢзў‘ж–Үж®ӢзјәпјҢж•…дёҖзӣҙжңӘиў«дё–дәәжүҖзҹҘгҖӮеҗҢж—¶пјҢеңЁдҝ®еҝ—жңҹй—ҙиў«еҸ‘зҺ°зҡ„иҝҳжңүиҘҝеұұеұұжһ—зӨәзҰҒзў‘е’ҢзҒөжіүеҜәзӨәзҰҒзў‘2еә§е‘ҠзӨәзў‘ж–ҮпјҢ3еә§зў‘ж–Үзҡ„еҸ‘зҺ°е’ҢдҝқжҠӨпјҢдёәз ”з©¶й„Ӯе·һең°ж–№еҸІеҝ—жҸҗдҫӣдәҶе®қиҙөзҡ„第дёҖжүӢиө„ж–ҷгҖӮ
вҖңжҲ‘зҡ„жң¬иҒҢе·ҘдҪңжҳҜж–Үзү©дҝқжҠӨпјҢеҸҜжҜ”иө·еҷЁзү©жң¬иә«зҡ„е®Ңж•ҙпјҢжҲ‘жӣҙж„ҝж„ҸеҒҡж–Үзү©иғҢеҗҺж–ҮеҢ–еҶ…ж¶өзҡ„е®ҲжҠӨиҖ…гҖӮвҖқиҝҷжҳҜзҶҠеҜҝжҳҢе…Ҳз”ҹеңЁйҮҮи®ҝдёӯеҸҚеӨҚиҜҙзҡ„дёҖеҸҘиҜқгҖӮвҖңеҸӨеҜәзҰ…жҲҝеҗҺзҡ„еЎ”жһ—еҹӢ葬зқҖеҺҶд»Јй«ҳеғ§зҡ„жі•иә«пјҢеЎ”еҹәйЈҺеҢ–жҚҹжҜҒеҫҲдёҘйҮҚпјҢйЎ¶йғЁеЎ”еҲ№дёҠи®°иҪҪзҡ„жҳҜй«ҳеғ§зҡ„姓еҗҚдёҺз”ҹе№іпјҢеҸҜеӨ§йғЁеҲҶйғҪиў«еұұжҙӘеҶІжҜҒпјҢеҜәеәҷе’Ңе°ҡеңЁдҝ®зј®ж—¶е·ҘдҪңдёҚз»ҶиҮҙпјҢи®ёеӨҡеЎ”еҲ№иў«йҡҸж„Ҹж‘Ҷж”ҫеңЁдёҚеҗҲзҡ„еЎ”иә«дёҠгҖӮвҖқиҜҙиө·иҝҷдәӣпјҢзҶҠеҜҝжҳҢж·ұж„ҹз—ӣжғңпјҢдёҚд»…д»…жҳҜдёәдҪӣеЎ”жң¬иә«зҡ„жҚҹжҜҒиҖҢжғӢжғңпјҢжӣҙеӨҡзҡ„жҳҜеҜ№еҺҶд»Јй«ҳеғ§иә¬иҖ•дёҖз”ҹзҡ„дёҚе№іе’ҢеҜ№еҪ“еүҚең°ж–№ж–Үзү©дҝқжҠӨзҺ°зҠ¶зҡ„ж— еҘҲгҖӮи°ҲеҸҠжңӘжқҘе·ҘдҪңзҡ„жү“з®—пјҢзҶҠеҜҝжҳҢиЎЁзӨәпјҢд»–жӯЈеңЁиҖғиҷ‘гҖҠ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еҝ—гҖӢзҡ„еҶҚзүҲпјҢеёҢжңӣжңүзӣёе…іиө„ж–ҷзҡ„еҗ„з•ҢдәәеЈ«иғҪдёҺд»–иҒ”зі»гҖӮ
1600дҪҷе№ҙзҡ„ж–—иҪ¬жҳҹ移пјҢеҸӨзҒөжіүеҜәи§ҒиҜҒдәҶй„Ӯе·һеӨӘеӨҡ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ҢиҖҢеҸӨеҜәиғҢеҗҺ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ҢеҲҷз”ұд»ҘзҶҠеҜҝжҳҢе…Ҳз”ҹдёәд»ЈиЎЁзҡ„й„Ӯе·һдҝ®еҝ—дәәжқҘе®ҲжҠӨгҖӮ
иҙЈд»»зј–иҫ‘пјҡйӮұиҸ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