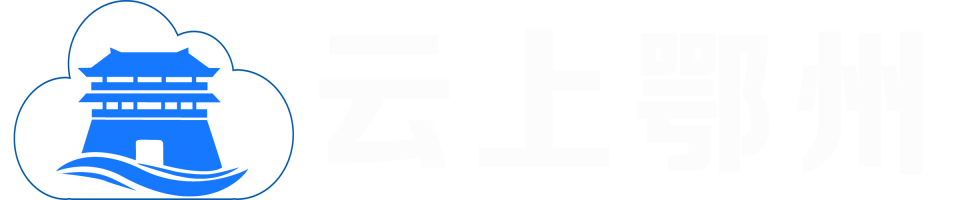жңҖйҡҫзҶ¬зҡ„йӮЈдәӣе№ҙпјҢиөөйҳҝе…°зңҹзҡ„жӢ…еҝғпјҢжҖ»жңүдёҖеӨ©дёҚжҳҜеүҚеӨ«жү“жӯ»дәҶеҘ№пјҢе°ұжҳҜеҘ№жқҖжӯ»д»–гҖӮ
他们зҰ»е©ҡ12е№ҙдәҶпјҢдҪҶж— и®әеҘ№еёҰзқҖеӯ©еӯҗжҗ¬еҲ°е“ӘйҮҢпјҢеүҚеӨ«жҖ»иғҪеҚғж–№зҷҫи®Ўжү“еҗ¬еҲ°еҘ№зҡ„иҗҪи„ҡеӨ„пјҢи·ҹиҝҮеҺ»пјҢеҗҢеҗғеҗҢдҪҸпјҢж—¶дёҚж—¶еҜ№еҘ№е®һж–Ҫж®ҙжү“гҖӮ
еҘ№иў«иҸңеҲҖйЎ¶иҝҮи„–еӯҗпјҢиў«зҒҢж»ЎејҖж°ҙзҡ„жҡ–еЈ¶з ёиҝҮеӨҙпјҢиў«иғ¶еёҰзј иҝҮжүӢи„ҡгҖӮеҘ№йҡҸжүӢжҢҮеҮәиә«дёҠзҡ„дјӨеҸЈпјҢжңүзҡ„зјқиҝҮй’ҲпјҢжңүзҡ„жІЎжңүгҖӮеҘ№ж„ҹж…ЁиҮӘе·ұе‘ҪеӨ§пјҢвҖңиҖҒеӨ©зҲ·з…§йЎҫвҖқгҖӮ
2016е№ҙ3жңҲ1ж—ҘпјҢгҖҠдёӯеҚҺдәәж°‘е…ұе’ҢеӣҪ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ж–ҪиЎҢгҖӮдёҖдёӘеӨҡжңҲеҗҺпјҢеҶ…и’ҷеҸӨдёҖ家ең°ж–№жі•йҷўдёӢиҫҫж°‘дәӢиЈҒе®ҡд№ҰпјҢзҰҒжӯўиөөйҳҝе…°зҡ„еүҚеӨ«вҖңйӘҡжү°гҖҒи·ҹиёӘгҖҒжҺҘи§Ұз”іиҜ·дәәеҸҠе…¶дәІеұһвҖқпјҢеҗҢж—¶иҙЈд»Өд»–жҗ¬иө°гҖӮ
еүҚеӨ«иө·еҲқиҝҳдёҚжңҚж°”гҖӮжі•е®ҳзҡ„еҠһе…¬е®ӨйҮҢпјҢд»–еңЁдәәиә«е®үе…ЁдҝқжҠӨд»ӨдёҠзӯҫдәҶеӯ—пјҢ然еҗҺеҪ“еңәе°Ҷиҝҷзәёж–Үд№ҰжҸүжҲҗдёҖеӣўпјҢжү”иҝӣдәҶеһғеңҫжЎ¶гҖӮ
еҸёжі•дәәе‘ҳеҸӘеҘҪеҗҢд»–и°ҲиҜқпјҢи®©д»–жҳҺзҷҪпјҢдҝқжҠӨд»Өз»қдёҚжҳҜдёҖзәёз©әж–ҮгҖӮж №жҚ®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пјҢеҰӮжһңиҝқеҸҚиҰҒжүҝжӢ…жі•еҫӢиҙЈд»»гҖӮд»–иҝҷжүҚвҖңжҖ•дәҶвҖқпјҢд»ҺеҘ№зҡ„з”ҹжҙ»дёӯж’ӨеҮәгҖӮ
вҖңжңүжҙ»и·ҜдәҶгҖӮвҖқиөөйҳҝе…°иҜҙгҖӮ
еҘ№зңӢеҲ°еүҚеӨ«з«ҷиө·жқҘпјҢйҡ”зқҖиҢ¶еҮ жҺўиҝҮиә«еӯҗжҠұдҪҸдәҶиҮӘе·ұгҖӮеӨ§еҘіе„ҝжғҠе‘јпјҡвҖңзҲёзҲёжҠҠеҰҲеҰҲзҡ„йј»еӯҗе’¬дёӢжқҘдәҶпјҒвҖқ
иө°дёҠиҝҷжқЎвҖңжҙ»и·ҜвҖқпјҢи®ёеӨҡдәәз”ЁдәҶеҫҲд№…гҖӮ
еҲ°2017е№ҙ3жңҲ1ж—ҘпјҢ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ж–ҪиЎҢдёҖе‘Ёе№ҙгҖӮеңЁиҝҷдёҖе№ҙдёӯпјҢз« е°Ҹдә‘зҡ„з”ҹжҙ»д»ҺеӨұжңӣпјҢеҲ°з»қжңӣпјҢеҶҚеҲ°йҮҚзҺ°еёҢжңӣгҖӮ
иҖҒ家еңЁйҮҚеәҶзҡ„еҘ№пјҢеүҚе№ҙе№ҙеә•е’ҢдёҲеӨ«зҰ»дәҶе©ҡгҖӮзҰ»е©ҡеүҚдёҲеӨ«жңҖеҗҺдёҖж¬ЎеҠЁжүӢжү“еҘ№пјҢжҳҜеӣ дёәеҘ№жү“з®—еңЁеӣҪеәҶй•ҝеҒҮжңҹй—ҙеӣһиҖҒ家зңӢжңӣзҲ¶жҜҚпјҢиҖҢд»–дёҚд№җж„ҸеҘ№еҺ»гҖӮ
жү“еҘ№зҡ„зҗҶз”ұпјҢеҮ д№ҺйғҪжҳҜиҝҷзұ»вҖңйёЎжҜӣи’ңзҡ®зҡ„е°ҸдәӢвҖқгҖӮ他第дёҖж¬ЎеҜ№з« е°Ҹдә‘еҠЁжүӢпјҢеҸӘжҳҜеӣ дёәеҘ№дёҚжғіи®©д»–жҠҠжіЎзқҖж–№дҫҝйқўзҡ„зў—пјҢжҗҒеңЁзӮүеӯҗдёҠжҷҫзқҖзҡ„йһӢеһ«дёҠгҖӮ
иҝҷж ·зҡ„жҡҙеҠӣд№ҹдёҚд»…й’ҲеҜ№еҘ№гҖӮеүҚеӨ«дјҡеӣ дёәд»–жҜҚдәІиҰҒеҺ»вҖңеҒҡзҗҶз–—вҖқиҖҢиҮӘе·ұдёҚеҗҢж„ҸпјҢе°ұжҺҖзҝ»е®¶йҮҢзҡ„йҘӯжЎҢпјҢй—№еҲ°жҜҚдәІеҗ“еҫ—з»ҷд»–и·ӘдёӢжүҚзҪўдј‘пјӣд»–д№ҹдјҡдёәдәҶйҖјиҝ«еүҚеҰ»и·ҹд»–иҒ”зі»пјҢи®©иҝҳеңЁдёҠе°ҸеӯҰзҡ„еҘіе„ҝпјҢи„–еӯҗдёҠжҢӮзқҖзүҢеӯҗи·ӘеңЁең°дёҠпјҢжӢҚдёӢз…§зүҮеҸ‘еңЁеҫ®дҝЎжңӢеҸӢеңҲйҮҢгҖӮ
他们жңү3дёӘеӯ©еӯҗгҖӮзҰ»е©ҡеҗҺпјҢз« е°Ҹдә‘дәүеҸ–еҲ°дәҶдёӨдёӘеҘіе„ҝзҡ„зӣ‘жҠӨжқғпјҢ3еІҒзҡ„е°Ҹе„ҝеӯҗеҲӨз»ҷдәҶеүҚеӨ«гҖӮеҘ№и§үеҫ—еүҚеӨ«дёҚдјҡеҜ№еҘіе„ҝеҘҪпјҢиҖҢе„ҝеӯҗд»–жҲ–и®ёвҖңдјҡзңӢйҮҚдәӣвҖқпјҢиғҪвҖңеҘҪеҘҪз…§йЎҫвҖқгҖӮ
еҺ»е№ҙеӨҸеӨ©пјҢеҘ№еҶҚж¬ЎиёҸи¶іеүҚеӨ«е®¶дёӯпјҢеҮҶеӨҮжҺҘиө°дёӨдёӘеҘіе„ҝгҖӮиҝӣйӮЈйҒ“й—Ёд№ӢеүҚпјҢеҘ№е·Із»Ҹе°ҪеҸҜиғҪең°иӯҰи§үпјҢжҸҗеүҚи®©дәІжҲҡ收иө·дәҶ家дёӯзҡ„жүҖжңүеҲҖе…·е’Ңе°–й”җзү©е“ҒгҖӮ
еҘ№еңЁжІҷеҸ‘дёҠеқҗзқҖпјҢдёӨдёӘеҘіе„ҝеҲҶеҲ«еқҗеңЁеҘ№иә«иҫ№гҖӮж»ЎеұӢеӯҗ家дәәеҠқеҘ№з»§з»ӯвҖңи·ҹд»–иҝҮвҖқпјҢвҖңдёәдәҶеӯ©еӯҗвҖқгҖӮеүҚеӨ«д№ҹеҜ№еҘ№иҜҙпјҢзҰ»е©ҡеҚҸи®®ж №жң¬вҖңжІЎз”ЁвҖқпјҢеҘ№иҝҳеҫ—еӣһжқҘгҖӮ
еҘ№еӣһзӯ”вҖңдҪ 们дёҚиҰҒеҶҚеҠқдәҶвҖқпјҢеҸҲеҸҚ问他们пјҢвҖңжҳҜиҰҒжҲ‘зҡ„е‘Ҫд№ҹдәӨеҫ…еңЁд»–жүӢйҮҢеҗ—вҖқпјҹ
йҡҸеҗҺеҘ№зңӢеҲ°еүҚеӨ«з«ҷиө·жқҘпјҢйҡ”зқҖиҢ¶еҮ жҺўиҝҮиә«еӯҗжҠұдҪҸдәҶеҘ№гҖӮеҘ№еҗ¬еҲ°еӨ§еҘіе„ҝзҡ„жғҠе‘јпјҡвҖңзҲёзҲёжҠҠеҰҲеҰҲзҡ„йј»еӯҗе’¬дёӢжқҘдәҶпјҒвҖқ
з« е°Ҹдә‘зҡ„йј»е°–гҖҒйј»зҝјгҖҒйј»е°ҸжҹұйғҪиў«е’¬жҺүдәҶпјҢйј»е°Ҹжҹұе°ҸиҪҜйӘЁеӨ–йңІпјҢдјӨеҠҝйүҙе®ҡз»“жһңжҳҜвҖңйҮҚдјӨдәҢзә§вҖқгҖӮжЈҖеҜҹйҷўжү№жҚ•дәҶеҘ№зҡ„еүҚеӨ«пјҢд»Ҙж¶үе«Ңж•…ж„ҸдјӨе®ізҪӘжҸҗиө·е…¬иҜүгҖӮд»–еңЁзңӢе®ҲжүҖйҮҢз»ҷеҘ№жү“дәҶз”өиҜқпјҢвҖңеҲ«жғіж‘Ҷи„ұжҲ‘пјҢиҝҷиҫҲеӯҗе°ұи·ҹдҪ иҝҮдәҶвҖқгҖӮ
еҚідҪҝе·Із»ҸиҝҮеҺ»дәҶеҚҠе№ҙпјҢжҸҗиө·йӮЈеӨ©еҸ‘з”ҹ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з« е°Ҹдә‘иҝҳжҳҜиғҪи®°иө·жҜҸдёҖдёӘз»ҶиҠӮгҖӮ
вҖңеҫҲеӨҡж—¶еҖҷпјҢ并дёҚжҳҜзҰ»е©ҡдәҶе°ұиғҪж‘Ҷи„ұжҺ§еҲ¶гҖӮвҖқеҢ—дә¬жәҗдј—жҖ§еҲ«еҸ‘еұ•дёӯеҝғдё»д»»жқҺиҺ№еҗ‘дёӯеӣҪйқ’е№ҙжҠҘВ·дёӯйқ’еңЁзәҝи®°иҖ…и§ЈйҮҠгҖӮ
жқҺиҺ№жҳҜз« е°Ҹдә‘зҡ„д»ЈзҗҶеҫӢеёҲпјҢеңЁиҝҷиө·жЎҲ件дёӯпјҢеҢ…жӢ¬жі•йҷўе’ҢжЈҖеҜҹйҷўе·ҘдҪңдәәе‘ҳеңЁеҶ…пјҢдәә们йғҪеңЁй—®пјҢдёәд»Җд№ҲиҝҷдёӨдёӘдәәе·Із»ҸзҰ»е©ҡдәҶпјҢд»Қ然算жҳҜ家жҡҙжЎҲ件呢пјҹ
вҖң他们确е®һдёҚжҳҜеҫҲзҗҶи§ЈгҖӮвҖқжқҺиҺ№еҸӘеҘҪдёҚж–ӯдҪңеҮәи§ЈйҮҠпјҢиҝҷз§Қжғ…еҶөпјҢеұһдәҺ家еәӯжҡҙеҠӣе®һж–ҪиҖ…иҝӣиЎҢзҡ„延з»ӯжҖ§дјӨе®ігҖӮ
2017е№ҙ1жңҲзҡ„дёҖдёӘжЎҲдҫӢпјҢиҜҙжҳҺ家жҡҙе®һж–ҪиҖ…зҡ„жҠҘеӨҚжңүеӨҡд№ҲеҸҜжҖ•пјҡ64еІҒзҡ„е№ҝиҘҝйҷҶе·қеҺҝйҖҖдј‘жі•е®ҳеӮ…жҳҺз”ҹеңЁе®¶дёӯйҒҮе®іпјҢзҠҜзҪӘе«Ңз–‘дәәйҫҷе»әжүҚпјҢжӯЈжҳҜеӮ…жҳҺз”ҹеңЁ22е№ҙеүҚе®ЎзҗҶзҡ„дёҖиө·еӣ 家жҡҙжҸҗиҜ·зҰ»е©ҡжЎҲ件зҡ„иў«е‘ҠгҖӮ
жқҺиҺ№и®ӨдёәпјҢеә”иҜҘжҠҠеүҚй…ҚеҒ¶гҖҒеүҚдәІеҜҶе…ізі»иҖ…е®һж–Ҫзҡ„延з»ӯжҖ§дјӨе®іпјҢд№ҹзәіе…Ҙ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зҡ„з»ҶеҲҷеҪ“дёӯгҖӮ
иөөйҳҝе…°зҡ„д»ЈзҗҶдәәгҖҒеҢ—дә¬е°ҡиЎЎеҫӢеёҲдәӢеҠЎжүҖеҫӢеёҲеЎ”жӢүпјҢд№ҹеңЁеҗ‘жі•йҷўе’ҢжЈҖеҜҹйҷўи§ЈйҮҠгҖӮ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规е®ҡпјҢвҖң家еәӯжҲҗе‘ҳд»ҘеӨ–е…ұеҗҢз”ҹжҙ»зҡ„дәәд№Ӣй—ҙе®һж–Ҫзҡ„жҡҙеҠӣиЎҢдёәпјҢеҸӮз…§жң¬жі•и§„е®ҡжү§иЎҢгҖӮвҖқиҝҷдёҖжқЎжӯЈеҘҪйҖӮз”ЁдәҺиөөйҳҝе…°зҡ„жғ…еҶөгҖӮеҘ№з”іиҜ·зҡ„иҝҷд»ҪвҖңйқһ家еәӯжҲҗе‘ҳе…ізі»дәәвҖқдәәиә«е®үе…ЁдҝқжҠӨд»ӨпјҢеңЁж•ҙдёӘеҶ…и’ҷеҸӨиҮӘжІ»еҢәпјҢйғҪжІЎжңүе…ҲдҫӢеҸҜеҫӘгҖӮ
жҚ®еҶ…и’ҷеҸӨиҮӘжІ»еҢәеҰҮиҒ”жқғзӣҠйғЁеүҜйғЁй•ҝйӯҸдә‘зҺІд»Ӣз»ҚпјҢ2016е№ҙпјҢеҶ…и’ҷеҸӨеҰҮиҒ”зі»зҙҜи®ЎжҺҘеҫ…家жҡҙжҠ•иҜү700еӨҡиө·пјҢеҚ дҝЎи®ҝжҺҘеҫ…зҡ„29пј…гҖӮе…¶дёӯпјҢиҮӘжІ»еҢәеҰҮиҒ”жң¬зә§жҺҘеҫ…家жҡҙдҝЎи®ҝжЎҲ件иҝ‘80件пјҢе…Ёе№ҙеё®еҠ©е®¶жҡҙеҸ—е®ідәәеҸ‘еҮәдәәиә«е®үе…ЁдҝқжҠӨд»Өе…ұ17д»ҪвҖ”вҖ”еҲ°2017е№ҙ2жңҲеә•еҸҲеўһеҠ дәҶдёӨд»ҪгҖӮ
еҶ…и’ҷеҸӨиҮӘжІ»еҢәеҸ‘еҮәзҡ„第дёҖеј дҝқжҠӨд»ӨпјҢд№ҹжҳҜеЎ”жӢүеҫӢеёҲвҖңи·‘дёӢжқҘвҖқзҡ„гҖӮеҺ»е№ҙ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дёҖз”ҹж•ҲпјҢеҘ№е°ұиө¶еҺ»жі•йҷўпјҢеё®иҮӘе·ұзҡ„委жүҳдәәжҸҗеҮәдәҶз”іиҜ·гҖӮ
еЎ”жӢүеҫӢеёҲиҝҳи®°еҫ—пјҢе°ұиҝһжі•е®ҳдёҖејҖе§ӢвҖңйғҪжңүзӮ№жҮөвҖқпјҢеӣ дёәеҪ“ж—¶еңЁеҹәеұӮжі•йҷўпјҢи°Ғд№ҹжІЎжҺҘи§ҰиҝҮиҝҷдёӘдёңиҘҝпјҢеӨ§е®¶вҖңйғҪдёҚзҹҘйҒ“иҜҘжҖҺд№ҲеҒҡдәҶвҖқгҖӮ
е…ЁеӣҪи®ёеӨҡең°ж–№зҡ„еҹәеұӮжү§жі•йғЁй—ЁпјҢжҠҠвҖң家еәӯжҡҙеҠӣвҖқеҪ“еҒҡвҖң家еҠЎдәӢе„ҝвҖқзҡ„зҺ°иұЎд»Қ然еӯҳеңЁ
еңЁдёӯеӣҪеӨ§йҷҶпјҢ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д»Һж— еҲ°жңүпјҢз»ҸеҺҶдәҶж•ҙж•ҙ20е№ҙгҖӮ
1995е№ҙпјҢ第еӣӣж¬Ўдё–з•ҢеҰҮеҘіеӨ§дјҡеңЁеҢ—дә¬еҸ¬ејҖпјҢи®ҫзҪ®дәҶдё“й—Ёзҡ„家еәӯжҡҙеҠӣзҡ„и®®йўҳгҖӮ家жҡҙзҡ„жҰӮеҝөпјҢејҖе§Ӣиҝӣе…ҘдёӯеӣҪдәәзҡ„и§ҶйҮҺгҖӮ
ж•ҙдёӘз«Ӣжі•зҡ„иҝҮзЁӢпјҢиў«жқҺиҺ№з§°дёәвҖңе®һи·өе…ҲиЎҢвҖқгҖӮжҚ®жқҺиҺ№д»Ӣз»ҚпјҢ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зҡ„е·ҘдҪңпјҢе’ҢжҺЁеҠЁ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зҡ„з«Ӣжі•пјҢе…¶е®һдёҖзӣҙеңЁеҗҢж—¶иҝӣиЎҢгҖӮ
вҖң1996е№ҙпјҢй•ҝжІҷеёӮдәәеӨ§йҰ–е…ҲеҸ‘еёғдәҶдёҖдёӘеҸҚ家жҡҙзҡ„еҶіи®®пјҢиҝҷе°ұжҳҜеҸҚ家жҡҙеңЁдёӯеӣҪеӨ§йҷҶжңҖж—©зҡ„иө·зӮ№пјҢйҡҸеҗҺи®ёеӨҡзңҒеёӮйғҪејҖе§Ӣи·ҹиҝӣгҖӮеңЁжі•еҫӢеұӮйқўдёҠзӘҒз ҙжҳҜеңЁ2001е№ҙпјҢгҖҠе©ҡ姻法гҖӢдҝ®жӯЈжЎҲжӯЈејҸд»Ҙжі•жқЎзҡ„еҪўејҸпјҢеҶҷжҳҺзҰҒжӯўе’Ңйў„йҳІе®¶еәӯжҡҙеҠӣгҖӮвҖқжқҺиҺ№иҜҙгҖӮ
жӯӨеҗҺпјҢгҖҠеҰҮеҘіжқғзӣҠдҝқйҡңжі•гҖӢгҖҠжңӘжҲҗе№ҙдәәдҝқжҠӨжі•гҖӢгҖҠж®Ӣз–ҫдәәдҝқйҡңжі•гҖӢе’ҢгҖҠиҖҒе№ҙдәәжқғзӣҠдҝқйҡңжі•гҖӢдёӯпјҢд№ҹйғҪйҷҶз»ӯеҠ е…ҘдәҶзҰҒжӯўе®һж–Ҫ家еәӯжҡҙеҠӣзҡ„еҶ…е®№гҖӮ
дҪҶз”ЁжқҺиҺ№зҡ„иҜқиҜҙпјҢиҝҷдәӣеҶ…е®№йғҪйқһеёёз®ҖеҚ•пјҢеҸӘжҳҜз®ҖеҚ•зҡ„вҖңзҰҒжӯўвҖқгҖӮиҖҢдё”пјҢеҪ“жЎҲеҚ·дёҠзҡ„зҷҪзәёй»‘еӯ—иҗҪеҲ°зҺ°е®һз”ҹжҙ»дёӯпјҢеҫҖеҫҖдёҚиғҪе°ҪеҰӮдәәж„ҸгҖӮ
е°Ҫз®Ў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дёӯпјҢ第еҚҒдә”жқЎжҳҺ确规е®ҡпјҢвҖңе…¬е®үжңәе…іжҺҘеҲ°е®¶еәӯжҡҙеҠӣжҠҘжЎҲеҗҺеә”еҪ“еҸҠж—¶еҮәиӯҰпјҢеҲ¶жӯўе®¶еәӯжҡҙеҠӣпјҢжҢүз…§жңү关规е®ҡи°ғжҹҘеҸ–иҜҒпјҢеҚҸеҠ©еҸ—е®ідәәе°ұеҢ»гҖҒйүҙе®ҡдјӨжғ…гҖӮвҖқдҪҶеңЁе…ЁеӣҪи®ёеӨҡең°ж–№зҡ„еҹәеұӮжү§жі•йғЁй—ЁпјҢжҠҠвҖң家еәӯжҡҙеҠӣвҖқеҪ“еҒҡвҖң家еҠЎдәӢе„ҝвҖқзҡ„зҺ°иұЎд»Қ然еӯҳеңЁгҖӮ
з« е°Ҹдә‘жӣҫе°қиҜ•иҝҮеңЁжҢЁжү“еҗҺжҠҘиӯҰгҖӮйӮЈжҳҜеңЁ2015е№ҙпјҢд№ҹжҳҜеҘ№е”ҜдёҖдёҖж¬ЎжҠҘиӯҰпјҢиҖҢиӯҰж–№еҚҙ并没жңүеҮәиӯҰгҖӮ
вҖңжҲ‘们йӮЈдёӘе°Ҹең°ж–№пјҢжү“иҖҒе©Ҷиҝҷж ·зҡ„дёҖдәӣе°ҸдәӢпјҢжІЎжңүзңҹжӯЈеҮәдәӢе„ҝ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иӯҰеҜҹд№ҹдёҚдјҡеңЁж„Ҹзҡ„пјҢжҜ•з«ҹеңЁеҶңжқ‘пјҢеӨ«еҰ»жү“жү“й—№й—№еёёжңүгҖӮвҖқз« е°Ҹдә‘иҜҙгҖӮ
иөөйҳҝе…°д№ҹдёҚжҳҜжІЎжңүеҜ»жұӮиҝҮеё®еҠ©пјҢеүҚдәӣе№ҙеҘ№д№ҹжӣҫжҠҘиҝҮиӯҰпјҢиў«еҪ“еҒҡвҖң家еҠЎдәӢе„ҝвҖқеӨ„зҗҶдәҶгҖӮеҘ№иҒ”зі»иҝҮеҰҮиҒ”пјҢз…§ж ·ж— еҸҜеҘҲдҪ•гҖӮеҘ№д№ҹжү“иҝҮжі•еҫӢжҸҙеҠ©зғӯзәҝз”өиҜқпјҢдҪҶеңЁ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еҮәзҺ°д№ӢеүҚпјҢд№ҹжІЎеҫ—еҲ°д»Җд№Ҳи§Ғж•Ҳзҡ„жҸҙеҠ©гҖӮ
зӣҙеҲ°еҺ»е№ҙ3жңҲпјҢиөөйҳҝе…°зңӢеҲ°ж–°й—»пјҢзҹҘйҒ“дәҶжңүдҝқжҠӨд»Өиҝҷз ҒдәӢе„ҝгҖӮеҘ№дё»еҠЁиҒ”зі»дәҶеЎ”жӢүеҫӢеёҲгҖӮвҖңдәә家е°ұиғҪз”іиҜ·жҲҗеҠҹпјҢжҲ‘д№ҹиҜ•иҜ•е‘—гҖӮвҖқ
вҖңеҫҲеӨҡдәәй—®иөөйҳҝе…°пјҢйғҪзҰ»е©ҡ12е№ҙдәҶпјҢдҪ е’ӢдёҚж—©е‘Ҡе‘ўпјҹйӮЈдәӣејәеҠҝзҡ„дәәпјҢдёҚзҗҶи§ЈејұеҠҝиҖ…зҡ„йҡҫеӨ„гҖӮвҖқеЎ”жӢүеҸ№жҒҜгҖӮжҸҗеҮәиҙЁз–‘зҡ„дәәдёӯпјҢз”ҡиҮіеҢ…жӢ¬еҹәеұӮеҸёжі•дәәе‘ҳгҖӮ
иҝҷз§ҚејұеҠҝиҖ…зҡ„йҡҫеӨ„пјҢз”ЁжқҺиҺ№зҡ„иҜқиҜҙпјҢеңЁеҝғзҗҶеӯҰдёҠз§°дёәвҖңд№ еҫ—жҖ§ж— еҠ©вҖқгҖӮ
иҝҷжҳҜдёҖз§ҚеҸҚеӨҚеӨұиҙҘеҗҺеұҲжңҚдәҺеӣ°еўғпјҢеҪўжҲҗзҡ„ж¶ҲжһҒеҝғжҖҒгҖӮеҠЁзү©е®һйӘҢдёӯпјҢиў«е…іеңЁз¬јеӯҗйҮҢеҸҚеӨҚз”өеҮ»зҡ„зӢ—пјҢеҚідҪҝеҗҺжқҘжү“ејҖз¬јеӯҗпјҢд№ҹдёҚдјҡйҖғи·‘пјҢеҸҚиҖҢвҖңеҖ’ең°е‘»еҗҹйўӨжҠ–вҖқгҖӮеҗҺжқҘзҡ„дәәдҪ“е®һйӘҢеҸ‘зҺ°пјҢиҝҷз§Қжғ…еҶөеңЁдәәзұ»иә«дёҠеҗҢж ·дјҡеҸ‘з”ҹгҖӮ
еҸ—жҡҙиҖ…д№ҹе®№жҳ“йҷ·е…ҘиҮӘеҚ‘гҖҒиҮӘиҙЈзҡ„еҝғжҖҒдёӯгҖӮиөөйҳҝе…°дёҖеәҰи§үеҫ—иҮӘе·ұвҖңдёўдәәвҖқпјҢи§үеҫ—дәІжҲҡжңӢеҸӢйғҪвҖңзңӢдёҚиө·иҮӘе·ұвҖқгҖӮе°Ҫз®ЎпјҢеҘ№жүҚжҳҜжІЎжңүиҝҮй”ҷзҡ„йӮЈдёҖж–№гҖӮ
вҖңдёӯеӣҪиҮӘеҸӨд»ҘжқҘе°ұжңүвҖҳжі•дёҚиҝӣ家门вҖҷзҡ„дј з»ҹпјҢвҖқжқҺиҺ№еҜ№иҝҷдёҖзӮ№ж„ҹеҲ°ж— еҘҲпјҢеҘ№иҜҙпјҢеӨ§еӨҡж•°ж–ҪжҡҙиҖ…пјҢдёҚдјҡеҺ»жү“еҗҢдәӢжңӢеҸӢпјҢдёҚдјҡеҺ»иЎ—дёҠжү“йҷҢз”ҹдәәпјҢеӣ дёәиҝҷж ·еҒҡзҡ„зҠҜзҪӘжҲҗжң¬еӨӘй«ҳгҖӮ
з”·жҖ§еҗҢж ·д№ҹдјҡжҲҗдёә家еәӯжҡҙеҠӣзҡ„еҸ—е®іиҖ…пјҢжҜ”еҰӮжңүдәәдјҡиў«еҰ»еӯҗе®һж–ҪзІҫзҘһжҡҙеҠӣгҖҒз»ҸжөҺжҺ§еҲ¶пјҢз”ҡиҮіиә«дҪ“жҡҙеҠӣгҖӮ
еҮәдәҺиҮӘе°Ҡе’ҢиҮӘеҚ‘зҡ„дәӨз»ҮеҝғжҖҒпјҢ他们жӣҙеҠ дёҚж„ҝеҜ»жұӮеё®еҠ©пјҢе°Ҷ被家жҡҙзҡ„дәӢжғ…е…¬д№ӢдәҺдј—гҖӮжқҺиҺ№жӣҫйҒҮеҲ°иҝҮдёҖдҪҚз”·жҖ§еҸ—жҡҙиҖ…пјҢиЎЈжңҚжҢЎзқҖзҡ„ең°ж–№йғҪжҳҜдјӨгҖӮд»–иҜҙ他并дёҚжҳҜжү“дёҚиҝҮеҰ»еӯҗпјҢеҸӘжҳҜдёҚж„ҝж„Ҹжү“пјҢеҚҙжҲҗдәҶжҡҙеҠӣзҡ„еҸ—е®іиҖ…гҖӮ
вҖң家еәӯжҡҙеҠӣзҡ„жң¬иҙЁжҳҜдёҖз§ҚжқғеҠӣжҺ§еҲ¶е…ізі»пјҢж–ҪжҡҙиҖ…йҖҡиҝҮжҡҙеҠӣзҡ„еҪўејҸжқҘжҺ§еҲ¶еҜ№ж–№гҖӮжңҖз»ҲдјҡйҖүжӢ©еҸҚжҠ—зҡ„еҸ—жҡҙиҖ…еҸӘжҳҜеҶ°еұұдёҖи§’пјҢе°ұз®—йҖүжӢ©дәҶеҸҚжҠ—е’Ңи„ұзҰ»е®¶жҡҙзҺҜеўғпјҢе№іеқҮд№ҹдјҡз»ҸеҺҶ7ж¬ЎеҸҚеӨҚгҖӮвҖқжқҺиҺ№иҜҙгҖӮ
еҘ№жҸҗеҲ°дәҶиҮӘе·ұжӯЈеңЁд»ЈзҗҶзҡ„еҸҰдёҖиө·жЎҲ件гҖӮеҪ“дәӢдәәе·Із»Ҹ60еӨҡеІҒдәҶпјҢеңЁй•ҝе№ҙзҙҜжңҲзҡ„家жҡҙдёӯдёҚж–ӯеҝҚеҸ—пјҢе·Із»ҸжҲҗдәҶд№ жғҜгҖӮеҪ“дәӢдәә40еӨҡеІҒзҡ„еҘіе„ҝжӣҫжҳҜвҖң家жҡҙзӣ®зқ№е„ҝз«ҘвҖқпјҢеҰӮд»ҠеңЁдёәжҜҚдәІеҘ”иө°пјҢз”іиҜ·зҰ»е©ҡгҖӮеҪ“дәӢдәәзҡ„е„ҝеӯҗеҗҢж ·жҳҜ家жҡҙеҸ—е®іиҖ…пјҢеңЁеӨҡе№ҙзҡ„иў«иҷҗеҫ…дёӯзҪ№жӮЈдәҶзІҫзҘһеҲҶиЈӮз—ҮгҖӮ
иҝҷдҪҚеҘіе„ҝиҜҙпјҢзӯүжҜҚдәІзҰ»дәҶе©ҡпјҢеҘ№е°ұз…§йЎҫжҜҚдәІпјҢз…§йЎҫејҹејҹгҖӮеҘ№иҜҙпјҢиҮӘе·ұвҖңиҝҷиҫҲеӯҗдёҚеҸҜиғҪз»“е©ҡдәҶвҖқгҖӮ
з«Ӣжі•еҸӘжҳҜдёӘејҖе§ӢпјҢи®©жі•еҫӢзңҹжӯЈиө·еҲ°йў„йҳІеҲ¶жӯўе®¶еәӯжҡҙеҠӣгҖҒдҝқжҠӨеҸ—жҡҙиҖ…е®үе…Ёзҡ„дҪңз”ЁпјҢиҝҳжңүжј«й•ҝзҡ„иҝҮзЁӢ
еңЁжҲҗдёәеҶ…и’ҷеҸӨиҮӘжІ»еҢәеҰҮиҒ”жі•еҫӢз»ҙжқғе№іеҸ°зҡ„еҝ—ж„ҝиҖ…д№ӢеүҚпјҢеЎ”жӢүжІЎжңүжғіеҲ°пјҢйҒӯеҸ—家еәӯжҡҙеҠӣзҡ„еҘіжҖ§жңүиҝҷд№ҲеӨҡпјҢе°ұеғҸе№ійқҷжө·йқўд№ӢдёӢзҡ„жҡ—жөҒпјҢиҝһжҺҘзқҖж·ұдёҚи§Ғеә•зҡ„й»‘жҡ—и§’иҗҪгҖӮ
第дёҖеӨ©еҸӮдёҺеҝ—ж„ҝе·ҘдҪңпјҢеҘ№дёҖдёӘдёҠеҚҲе°ұжҺҘеҫ…дәҶ4еҗҚеҸ—жҡҙиҖ…пјҢи§үеҫ—вҖңж•ҙдёӘдәәйғҪжҷ•дәҶвҖқгҖӮеҲ°дёӯеҚҲпјҢеЎ”жӢүиҝһйҘӯйғҪеҗғдёҚдёӢеҺ»пјҢеҸӘе–қдәҶеҮ еҸЈж°ҙгҖӮ
вҖңжҲ‘们жҸҗеҖЎзҡ„жҳҜпјҢеҸ—е®іиҖ…еҜ№е®¶еәӯжҡҙеҠӣйӣ¶е®№еҝҚгҖӮвҖқеЎ”жӢүиҜҙгҖӮ
жҲӘиҮі2017е№ҙ2жңҲ28ж—ҘпјҢдёӯеӣҪиЈҒеҲӨж–Үд№ҰзҪ‘дёҠ已收еҪ•ж¶үеҸҠвҖңдәәиә«е®үе…ЁдҝқжҠӨд»ӨвҖқзҡ„жі•еҫӢж–Үд№Ұ350д»ҪгҖӮ
вҖңе…ій”®жҳҜжі•еҫӢзҡ„иҙҜеҪ»е®һж–ҪгҖӮвҖқж№–еҚ—зңҒеҰҮиҒ”жқғзӣҠйғЁйғЁй•ҝеҪӯиҝӘеҜ№дёӯеӣҪйқ’е№ҙжҠҘВ·дёӯйқ’еңЁзәҝи®°иҖ…иҜҙпјҢвҖңеҘҪзҡ„жі•еҫӢжқЎж–ҮиҰҒиҗҪе®һеҲ°жҜҸдёҖдёӘдёӘжЎҲдёӯеҺ»пјҢ并дёҚжҳҜ件容жҳ“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зҺ°е®һдёӯзҡ„жЎҲдҫӢеҚғе·®дёҮеҲ«пјҢжІЎжңүдёҖдёӘжҳҜе®Ңе…ЁзӣёеҗҢзҡ„пјҢеӣ жӯӨз«Ӣжі•еҸӘжҳҜдёӘејҖе§ӢпјҢи®©жі•еҫӢзңҹжӯЈиө·еҲ°йў„йҳІеҲ¶жӯўе®¶еәӯжҡҙеҠӣгҖҒдҝқжҠӨеҸ—жҡҙиҖ…е®үе…Ёзҡ„дҪңз”ЁпјҢиҝҳжңүжј«й•ҝзҡ„иҝҮзЁӢгҖӮвҖқ
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зҡ„еҸ‘еёғпјҢи®©дёҖзӣҙд»ҺдәӢеҸҚ家жҡҙе·ҘдҪңзҡ„еҪӯиҝӘвҖңеӨҮеҸ—йј“иҲһе’ҢжҝҖеҠұвҖқгҖӮиҝҷдёҖе№ҙйҮҢеҘ№жҳҺжҳҫж„ҹеҲ°пјҢ家еәӯжҡҙеҠӣзҡ„зӨҫдјҡе…іжіЁеәҰжӣҙй«ҳдәҶпјҢеҸ—жҡҙеҰҮеҘізҡ„жұӮеҠ©ж„ҸиҜҶд№ҹжҸҗй«ҳдәҶпјҢ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жҳҜпјҢвҖңиҒҢиғҪйғЁй—Ёзҡ„йҮҚи§ҶзЁӢеәҰе’Ңе·ҘдҪңз§ҜжһҒжҖ§жҳҺжҳҫеўһејәдәҶвҖқгҖӮ
е…ЁеӣҪеҰҮиҒ”еҗ‘дёӯеӣҪйқ’е№ҙжҠҘВ·дёӯйқ’еңЁзәҝи®°иҖ…жҸҗдҫӣзҡ„ж•°жҚ®жҳҫзӨәпјҢжҲӘиҮі2016е№ҙ11жңҲеә•пјҢе…ЁеӣҪе…ұжңү17дёӘзңҒ(еҢәеёӮ)пјҢе…ұи®ЎеҮәеҸ°дәҶ110д»ҪиҙҜеҪ»е®һж–Ҫ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зҡ„й…ҚеҘ—ж–Ү件гҖӮ
жқҺиҺ№жңҹеҫ…еӣҪ家иҝӣдёҖжӯҘеҲ¶е®ҡе’ҢжҺЁиЎҢгҖҠеҸҚ家еәӯжҡҙеҠӣжі•гҖӢзҡ„е®һж–Ҫз»ҶеҲҷгҖӮвҖңжҲ‘们зҺ°еңЁе°ұжҳҜиҰҒйҖҡиҝҮз«Ӣжі•пјҢжҸҗй«ҳ家еәӯжҡҙеҠӣзҡ„зҠҜзҪӘжҲҗжң¬гҖӮвҖқ
жҚ®еҘ№и§ЈйҮҠпјҢйңҖиҰҒжӣҙ新家еәӯжҡҙеҠӣзҡ„е®ҡд№үпјҢйҷӨдәҶиә«дҪ“жҡҙеҠӣе’Ңз»ҸжөҺжҺ§еҲ¶пјҢд№ҹеә”еҪ“жҠҠжҖ§жҡҙеҠӣгҖҒзІҫзҘһжҡҙеҠӣзәіе…Ҙ家жҡҙиҢғз•ҙ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дҝқжҠӨд»ӨеҲ¶еәҰгҖҒжі•еҫӢжҸҙеҠ©зӯүе…·дҪ“зҡ„规еҲҷпјҢд№ҹйңҖиҰҒжӣҙеҠ з»ҶеҢ–гҖӮ
еҘ№дёҫдәҶдёӘдҫӢеӯҗгҖӮе°Ҫз®Ўдәәиә«е®үе…ЁдҝқжҠӨд»ӨйҖҒиҫҫеҗҺпјҢвҖңз”ұдәәж°‘жі•йҷўжү§иЎҢпјҢе…¬е®үжңәе…ід»ҘеҸҠеұ…民委е‘ҳдјҡгҖҒжқ‘民委е‘ҳдјҡзӯүеә”еҪ“еҚҸеҠ©жү§иЎҢвҖқпјҢдҪҶе…·дҪ“е®һж–Ҫзҡ„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ёҖж–№йқўжҳҜжү§жі•жҲҗжң¬еӨӘй«ҳпјҢиӯҰеҠӣдёҚи¶іпјҢзјәд№Ҹзӣ‘зқЈпјҢеҸҰдёҖж–№йқўд№ҹжІЎжңүе…·дҪ“еҲ’еҲҶжқғиҙЈгҖӮ
вҖңзҺ°еңЁеҮ д№ҺжҳҜе…ЁзңӢеҪ“дәӢдәәжҳҜдёҚжҳҜе®іжҖ•жі•еҫӢпјҢиҮӘе·ұй…ҚдёҚй…ҚеҗҲжү§иЎҢгҖӮжҲ‘жӢ…еҝғзҡ„жҳҜпјҢеҪ“他们еҸ‘зҺ°пјҢи§ҰзҠҜдәҶдҝқжҠӨд»ӨпјҢеҸӘиҰҒжІЎжңүжһ„жҲҗзҠҜзҪӘпјҢд№ҹеҸӘжҳҜеҸ—еҲ°еҸёжі•ејәеҲ¶жҺӘж–ҪпјҢжҜ”еҰӮзҪҡж¬ҫпјҢжңҖеӨҡеҚҒдә”ж—Ҙд»ҘдёӢжӢҳз•ҷпјҢз”ҡиҮіеҫҲеӨҡжІЎжңүзңҹжӯЈжү§иЎҢгҖӮ他们е°ұдјҡи§үеҫ—пјҢд№ҹжІЎд»Җд№ҲдәӢе„ҝеҳӣпјҒиҝҷдёӘжі•еҫӢзҡ„жқғеЁҒжҖ§е°ұдјҡеҸ—еҲ°иҙЁз–‘пјҢдҝқжҠӨд»Өе°ұзңҹзҡ„жҲҗдәҶдёҖзәёз©әж–ҮгҖӮвҖқ
жқҺиҺ№зҡ„зЎ®йҒҮеҲ°иҝҮиҝҷж ·зҡ„жЎҲеӯҗгҖӮеҘ№дёәдёҖдҪҚеҸ—жҡҙиҖ…з”іиҜ·еҲ°дәҶдҝқжҠӨд»ӨпјҢдҪҶиҝҷдҪҚеҸ—жҡҙиҖ…зҡ„дёҲеӨ«з”Ёеӯ©еӯҗеЁҒиғҒеҘ№пјҢиҝ«дҪҝеҰ»еӯҗеӣһеҲ°дәҶд»–зҡ„жҺ§еҲ¶д№ӢдёӢгҖӮжқҺиҺ№е·Із»ҸиҒ”зі»дёҚеҲ°еҘ№дәҶгҖӮ
з« е°Ҹдә‘дҫқ然еҜ№жңӘжқҘжҖҖжңүдәӣи®ёжҒҗжғ§пјҢеҒ¶е°”иҝҳдјҡеҒҡжҒ¶жўҰпјҢеҘ№д№ҹжғіеҲ°иҝҮпјҢеүҚеӨ«жҖ»жңүдёҖеӨ©иҝҳдјҡд»ҺзүўйҮҢеҮәжқҘпјҢйӮЈд№ӢеҗҺиҜҘжҖҺд№ҲеҒҡпјҢеҘ№зҺ°еңЁвҖңйЎҫдёҚдәҶиҝҷд№ҲеӨҡдәҶвҖқгҖӮ
еҘ№ж јеӨ–жӢ…еҝғеӯ©еӯҗзҡ„еҝғзҗҶеҒҘеә·й—®йўҳгҖӮдёӨдёӘеҘіе„ҝеңЁеҘ№иә«иҫ№пјҢдҪҶ3еІҒзҡ„е„ҝеӯҗеңЁзҲ·зҲ·еҘ¶еҘ¶е®¶гҖӮеҘ№жӢ…еҝғпјҢд№ҹи®ёжІЎд»Җд№ҲжңәдјҡеҶҚи§ҒеҲ°е„ҝеӯҗдәҶгҖӮ
вҖңжҲ‘ж— иғҪдёәеҠӣдәҶгҖӮвҖқжҺҘеҸ—дёӯеӣҪйқ’е№ҙжҠҘВ·дёӯйқ’еңЁзәҝи®°иҖ…йҮҮи®ҝж—¶пјҢз« е°Ҹдә‘зҡ„зңјжіӘзһ¬й—ҙжөҒдәҶдёӢжқҘпјҢж— жі•еҶҚиҜҙдёӢеҺ»дәҶгҖӮ
вҖңдёҚиҰҒж”ҫејғиҮӘе·ұгҖӮвҖқиөөйҳҝе…°еёҢжңӣеҜ№иҝҷдәӣдёҺеҘ№жңүзқҖзӣёдјјз»ҸеҺҶзҡ„еҸ—жҡҙиҖ…иҜҙпјҢвҖңиҮӘе·ұжҙ»еҘҪдәҶжҜ”е•ҘйғҪејәгҖӮвҖқ
иөөйҳҝе…°ејҖе§ӢдәҶж–°з”ҹжҙ»пјҢиҝҮеҺ»зҡ„дёҖеҲҮпјҢжҲҗдәҶи®©еҘ№вҖңдёҚеҺ»жғід№ҹдёҚж•ўеҺ»жғівҖқзҡ„еҷ©жўҰгҖӮеҘ№жү“зқҖйӣ¶е·Ҙдҫӣе„ҝеӯҗиҜ»жҠҖж ЎпјҢи§үеҫ—иҷҪ然ж—ҘеӯҗиҝҮеҫ—иҫӣиӢҰпјҢдҪҶеҘ№з»ҲдәҺжңүеә•ж°”пјҢеңЁеӨӘйҳіеә•дёӢжҢәиғёжҠ¬еӨҙдәҶгҖӮеҘ№жғіи®©жүҖжңүдәІжҲҡжңӢеҸӢпјҢйғҪжқҘзңӢзңӢзҺ°еңЁзҡ„иҮӘе·ұгҖӮ
пјҲдёәдҝқжҠӨеҸ—и®ҝдәәйҡҗз§ҒпјҢж–Үдёӯиөөйҳҝе…°гҖҒз« е°Ҹдә‘зі»еҢ–еҗҚ зј–иҫ‘зҶҠи”ҡпј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