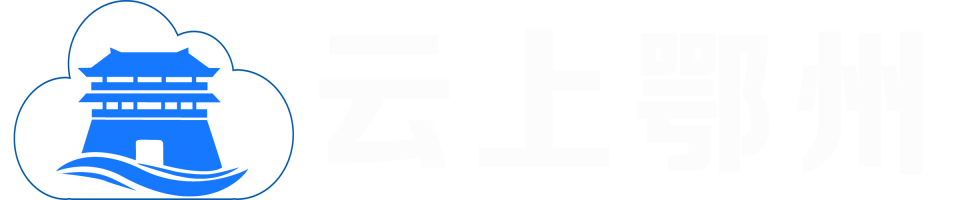жү“з«Ҙе№ҙж—¶д»Јиө·пјҢе°ұжҠҠдёӯз§Ӣзҡ„жҳҺжңҲзңӢеҫ—зү№еҲ«зҘһеңЈгҖӮдёӯз§Ӣзҡ„жңҲдә®пјҢжҫ„жҳҺгҖҒ银дә®гҖҒжө‘еңҶгҖҒй«ҳиҝңпјҢеҘ№е®ҒйқҷиҖҢе®үзҘҘпјҢзҫҺдёҪиҖҢз«Ҝеә„гҖӮеҘ№жҳҜдёҖе№ҙдёӯжңҖиғҪд»ЈиЎЁж°‘еҝғжүҖеҗ‘зҡ„еӣўеңҶпјҢжҳ з…§зқҖдәәдё–й—ҙзҡ„зҰ»еҗҲжӮІж¬ўгҖӮ
ж–°дёӯеӣҪиҜһз”ҹйӮЈе№ҙпјҢжҲ‘жүҚ6еІҒпјҢ6еІҒзҡ„ж—¶еҖҷжҲ‘дјҡиғҢиҜөдёҖдәӣйўӮжңҲе’ҸжңҲзҡ„е”җиҜ—гҖӮжҲ‘жЁЎд»ҝиҝҮжқҺзҷҪвҖңдёҫжқҜйӮҖжҳҺжңҲвҖқзҡ„зҘһжҖҒпјӣжҲ‘еҜ»жүҫиҝҮзҺӢз»ҙвҖңжҳҺжңҲжқҫй—ҙз…§вҖқзҡ„ж„ҸеўғгҖӮй•ҝеӨ§еҗҺпјҢжҲ‘еңЁдёӯз§Ӣд№ӢеӨңпјҢдёҺзҲ¶жҜҚе…„ејҹеҗҢиөҸдёҖиҪ®еңҶжңҲпјҢе…ұе“ҒдёҖеқ—жңҲйҘјгҖӮдёӯз§ӢжҳҺжңҲйҮҢзҡ„йЈҺжҷҜдәәзү©пјҢеңЁиҖҒдәә们зҘһиҜқеҜ“иЁҖиҲ¬зҡ„и®Іиҝ°дёӯпјҢжҙ»зҒөжҙ»зҺ°ең°иө°иҝӣжҲ‘зҡ„и®°еҝҶгҖӮжҲ‘и®°еҫ—е«ҰеЁҘгҖҒи®°еҫ—еҗҙеҲҡгҖҒи®°еҫ—еј жһңиҖҒпјҢиҝҳжңүйӮЈжЈөзҘһеҘҮзҡ„жЎӮиҠұж ‘гҖӮдёӯз§ӢжҳҺжңҲз»ҷжҲ‘еёҰжқҘдәҶеҜ№еӣўеңҶгҖҒеҗүзҘҘзҡ„еҗ‘еҫҖпјҢеҜ№зҫҺеҘҪзҲұжғ…зҡ„жҶ§жҶ¬е’ҢиҝҪжұӮпјҢеҜ№жЎӮиҠұй…’йҰҷзҡ„з”ңзҫҺжғіиұЎпјҢеҜ№е№ҝеҜ’е®«йҮҢе«ҰеЁҘзҡ„еҗҢжғ…е’ҢзҲұж…•гҖӮ
й•ҝеӨ§дәҶпјҢжҲ‘жңүдәҶеұһдәҺжҲ‘зҡ„вҖңе«ҰеЁҘвҖқпјҢеҘ№дёҚеңЁжңҲе®«пјҢеҘ№е°ұеңЁжҲ‘зҡ„иә«иҫ№гҖӮеҘ№жІЎжңүе«ҰеЁҘйӮЈд№ҲеӨҡзҡ„еҜӮеҜһдёҺеҝ§ж„Ғ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е«ҰеЁҘйӮЈд№ҲеӨҡзҡ„й—Іжғ…йӣ…и¶ЈпјҢеҘ№жҜҸеӨ©еҫҲеҝҷпјҢз”ЁзҺ°д»ЈиҜқжқҘиҜҙпјҢеҘ№жҜҸеӨ©еңЁеҝҷвҖңйқһйҒ—ж–ҮеҢ–зҡ„дј жүҝвҖқвҖ”вҖ”вҖ”еңЁдёҖжһ¶еҸӨиҖҒзҡ„з»ҮеёғжңәдёҠпјҢеҘ№жҜҸеӨ©дёҚи®ЎжҷЁжҳҸпјҢд»Ҙдәәй—ҙвҖңз»ҮеҘівҖқзҡ„еӢӨеӢүпјҢжҠӣеҠЁдёҖжҠҠе°ҸиҲ№дјјзҡ„жўӯеӯҗпјҢз»ҮеҮәдёҖеҚ·еҚ·иҠұиүІйІңдёҪгҖҒиҙЁең°дёҠд№ҳзҡ„еёғеҢ№пјҢиөўеҫ—еӣӣд№Ўе©Ҷе§Ёе°Ҹ姑зҡ„жҢ‘йҖүдёҺз§°иөһгҖӮ
еҪ“然пјҢжҲ‘们清иҙ«гҖҒе№ёзҰҸзҡ„ж—Ҙеӯҗд№ҹдёҚд№ҸиҜ—ж„ҸпјҢеңЁжңүжңҲдә®зҡ„еӨңжҷҡпјҢжҲ‘е’ҢжҲ‘зҡ„вҖңе«ҰеЁҘвҖқдјҡжҠ–иҗҪдёҖиә«з–Ід№ҸпјҢжүӢзүөжүӢең°д»ҺеҘ№еұ…дҪҸзҡ„е°ҸиЎ—пјҢиө°еҗ‘жҲ‘иҜ—ж„ҸзӣҺ然зҡ„е°Ҹй•ҮпјҢ5е…¬йҮҢзҡ„и·ҜзЁӢпјҢжҲ‘们еҫңеҫүеңЁжңҲиүІеҰӮж°ҙзҡ„е…¬и·ҜдёҠ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д»Із§Ӣж—¶иҠӮпјҢеҮүйЈҺд№ д№ пјҢз§Ӣиҷ«е”§е”§пјҢеӨҙйЎ¶жҳҹе…үй—ӘиҖҖпјҢи„ҡдёӢйңІдјјзҸҚзҸ пјҢзңҹжҳҜи®©дәәеҝғйҶүзҘһиҝ·е‘ҖгҖӮжңҲиүІжңҰиғ§дёӯпјҢд»»дҪ•и„ёиүІгҖҒзңјиүІйғҪжҳҜжё©жҹ”еҸӢе–„зҡ„пјҢжІЎжңүжӯ§и§ҶпјҢжІЎжңүзӣҜжўўпјҢжңҲе…үдёӢзҡ„ж•…д№Ўи®©дәәжғіиө·жҷ®еёҢйҮ‘笔дёӢзҡ„ж¶…з“ҰжІіе°Ҹжқ‘гҖӮ
жңүдәәиҜҙпјҢжңҲдә®жҳҜдёӯз§ӢиҠӮзҡ„вҖңеҘізҡҮвҖқпјҢеҸҜжҳҜдәәдё–й—ҙе“ӘжңүйӮЈд№ҲеӨҡеҰӮж„Ҹзҡ„дәӢпјҹвҖңжңҲжңүйҳҙжҷҙеңҶзјәпјҢдәәжңүжӮІж¬ўзҰ»еҗҲвҖқпјҢжІЎжңүжңҲдә®зҡ„дёӯз§ӢиҠӮжҜ•з«ҹиҝҳжҳҜеӯҳеңЁзҡ„гҖӮйӮЈжҳҜвҖңеӣӣдәәеё®вҖқжЁӘиЎҢзҡ„е№ҙжңҲпјҢжҲ‘еӣ дёәз”ҹи®ЎпјҢиғҢдә•зҰ»д№ЎеӨ–еҮәеҒҡиӢҰеҠӣпјҢдёҚи®°еҫ—ж—¶еәҸжөҒиҪ¬пјҢж·ЎеҝҳдәҶжҳҘеӨҸз§ӢеҶ¬пјҢеҸӘжңүеҪ“еҶңеҺҶе…«жңҲеҚҒдә”зҡ„жңҲдә®йңІеҮәжҜҚдәІиҲ¬ж…ҲзҲұзҡ„и„ёеәһж—¶пјҢжүҚзҢӣ然й—ҙе”ӨйҶ’жҲ‘еҜ№дәІдәәзҡ„жҖқеҝөпјҢеҜ№еӣўеңҶзҡ„зҘҲзӣјпјҢеҜ№еҝғдёӯвҖңз§Ӣж°ҙдјҠдәәвҖқзҡ„ж·ұжғ…еҗҹе”ұгҖӮиҝҷж—¶еҖҷпјҢжҲ‘дјҡиө°еҮәе·ҘжЈҡпјҢжқҘеҲ°жңҲдә®ж№ҫзҡ„й•ҝе ӨдёҠпјҢйқўеҜ№еӨ©дёҠзҡ„йӮЈиҪ®еңҶжңҲпјҢеҸҢжүӢеҗҲжҺҢпјҢй»ҳй»ҳеҝөеҮәеҝғдёӯзҡ„зҫҺеҘҪзҘқзҰҸе’Ңж·ұи—Ҹзҡ„еҝғж„ҝгҖӮеҸӘжңүиҝҷдёҖеҲ»пјҢжҲ‘жүҚж„ҹеҲ°иӢҸиҪјзҡ„вҖңдҪҶж„ҝдәәй•ҝд№…пјҢеҚғйҮҢе…ұе©өеЁҹвҖқйҒ“еҮәдәҶжҷ®еӨ©дёӢжүҖжңүжёёеӯҗзҡ„еҝғеЈ°гҖӮ
жҲ‘35еІҒйӮЈе№ҙпјҢеҚі1978е№ҙпјҢжҳҜдёӯеӣҪзҺ°д»ЈеҸІдёҠ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е№ҙд»Ҫд№ӢдёҖгҖӮиҝҷдёҖе№ҙзҡ„2жңҲ17ж—ҘпјҢгҖҠдәәж°‘ж—ҘжҠҘгҖӢе…Ёж–ҮиҪ¬иҪҪдәҶеҫҗиҝҹзҡ„еӨ§еһӢжҠҘе‘Ҡж–ҮеӯҰгҖҠе“Ҙеҫ·е·ҙиө«зҢңжғігҖӢпјҢжӢЁд№ұеҸҚжӯЈпјҢ第дёҖж¬ЎеҜ№дёҖдёӘжңүдәүи®®зҡ„科еӯҰе·ҘдҪңиҖ…дҪңдәҶж·ұжғ…зҡ„и®ҙжӯҢпјӣ1978е№ҙпјҢе®үеҫҪеҮӨйҳіе°ҸеІ—жқ‘18дҪҚеҶңж°‘еңЁеңҹең°жүҝеҢ…иҙЈд»»д№ҰдёҠжҢүдёӢзәўжүӢеҚ°пјҢиҝҷдёҖвҖңжҢүвҖқпјҢж”№еҸҳдәҶдёӯеӣҪеҶңжқ‘еҸ‘еұ•еҸІпјӣ1978е№ҙпјҢдёӯе…ұдёӯеӨ®еҸ¬ејҖдәҶеҚҒдёҖеұҠдёүдёӯе…ЁдјҡпјҢйҮ‘й’ҹе“ҚеҪ»е…Ёдё–з•ҢпјҢдёӯеӣҪ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зҡ„е·ЁиҪ®жү¬еёҶеҗҜиҲӘдәҶгҖӮиҝҷдёҖе№ҙзҡ„дёӯз§ӢиҠӮпјҢжҲ‘收еҲ°дәҶжҒўеӨҚзЁҝиҙ№еҲ¶еәҰеҗҺзҡ„第дёҖеј зЁҝиҙ№йҖҡзҹҘеҚ•пјҢжҲ‘з”Ёе®ғд№°дәҶдёҖзӣ’жӯҰжұүеҶ з”ҹеӣӯзҡ„жңҲйҘјпјҢиҝһеӨңиө¶еӣһиҖҒ家пјҢеңЁдё№жЎӮйЈҳйҰҷзҡ„еҗҺйҷўпјҢжҲ‘дёҺд№…еҲ«зҡ„家дәәеӣўеңҶеңЁжңҲе…үдёӢзҡ„е°Ҹж–№жЎҢеүҚпјҢдёҖиҫ№е“Ғе°қжңҲйҘјпјҢдёҖиҫ№з•…еҸҷжғ…жҖҖгҖӮжҲ‘е‘ҠиҜүжҲ‘ж»Ўи„ёжІ§жЎ‘зҡ„зҲ¶жҜҚеҸҢдәІпјҢжҲ‘е°ҶеҫҲеҝ«з»“жқҹжөӘиҝ№еӨ©ж¶Ҝзҡ„з”ҹжҙ»пјҢеӣһеҲ°жҲ‘ж•…д№Ўжё©жҡ–зҡ„жҖҖжҠұгҖӮ
иҖҢд»ҠпјҢжҲ‘ж— йЎ»дёәжҠ’еҸ‘еҝғдёӯзҡ„еҝ§жӮ’иҖҢеҗҹе”ұвҖңжҳҺжңҲеҮ ж—¶жңүвҖқзҡ„вҖңж°ҙи°ғжӯҢеӨҙвҖқдәҶгҖӮжҜҸеҪ“дёӯз§ӢеҲ°жқҘзҡ„ж—¶еҲ»пјҢжҲ‘еҗҢжҲ‘зҡ„家дәәеҖҚеҠ зҸҚжғңзҡ“жңҲеҪ“з©әдёӢзҡ„жҜҸеҜёе…үйҳҙпјҢйқўеҜ№еӨҙйЎ¶зҡ„е©өеЁҹеҪ©дә‘пјҢжҲ‘иҷ”иҜҡең°зҘҲзҘ·пјҡж„ҝеӨ©дёӢзҡ„дәІжңӢеҘҪеҸӢе’ҢдёҖеҲҮе–„иүҜзҡ„дәә们пјҢе…ұдә«дёӯз§ӢжңҲеңҶзҡ„жё©йҰЁпјҢи®©е№ёзҰҸеҗүзҘҘж°ёй©»еҝғдёӯгҖӮ
дҪңиҖ…пјҡе§ңй”Ӣйқ’
иҙЈд»»зј–иҫ‘пјҡзҪ—зҗјж•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