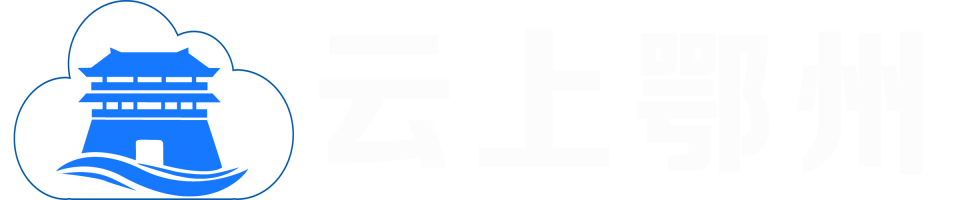зҪҗеӨҙ瓶装зқҖжҲ‘з”ҹе‘ҪдёӯжңҖйҡҫеҝҳзҡ„дёҖж®өеҝғи·ҜеҺҶзЁӢпјҢйҮҢйқўжңүжҲ‘жӣҫз»Ҹзҡ„йҹ¶еҚҺгҖӮ
45е№ҙеүҚпјҢж°ҙжһңзҪҗеӨҙж—ўжҳҜеӯ©еӯҗ们зҡ„жғҰи®°пјҢд№ҹжҳҜзңӢз—…дәәгҖҒйҖҒиҠӮзӨјзҡ„йҰ–йҖүгҖӮйӮЈж—¶зҡ„ж°ҙжһңзҪҗеӨҙйғҪжҳҜз”Ёи–„й“Ғзҡ®еҺӢе°ҒпјҢеӨ§дәәз”ЁиҸңеҲҖејҖ瓶пјҢеңЁй“Ғзҡ®дёҠеҠҲеҮәдёҖдёӘвҖңеҚҒвҖқеӯ—пјҢеҶҚж…ўж…ўз”ЁжүӢжҺ°ејҖпјҢйӮЈеҜ№и§’еҫҲй”ӢеҲ©пјҢдёҖдёҚе°ҸеҝғдјҡжҠҠжүӢеҲ’еҮәиЎҖгҖӮзҪҗеӨҙеҗғе…үдәҶпјҢ瓶еӯҗиҝҳиҲҚдёҚеҫ—дёўпјҢжҙ—дәҶжҙ—е°ұжҲҗдәҶжҲ‘们д№ҰеҢ…йҮҢзҡ„зІҫй…Қ件вҖ”вҖ”вҖ”вҖңзҪҗеӨҙиҸңвҖқпјҢе…¶е®һе°ұжҳҜдёҖзҪҗи…ҢиҸңгҖӮ
1972е№ҙжҳҘиҠӮеҲҡиҝҮпјҢи®ёеӨҡеҗҢйҫ„дәәиө°иҝӣдәҶжҶ§жҶ¬зҡ„ж®өеә—й«ҳдёӯгҖӮ2е№ҙеӨҡзҡ„й«ҳдёӯдҪҸж Ўз”ҹжҙ»пјҢеҜ№дәҺйӮЈдёӘж—¶д»Јзҡ„жҲ‘们пјҢж„Ҹе‘ізқҖжҙ»еҠӣдёҺз”ҹеҠЁгҖӮиҖҢйӮЈдёӘе№іе№іж·Ўж·Ўзҡ„зҪҗеӨҙ瓶пјҢеҲҷиЈ…зқҖжҲ‘们зҡ„йҹ¶еҚҺпјҢиЈ…зқҖжҲ‘们жҲҗй•ҝзҡ„иҪЁиҝ№гҖӮ
дёҠдё–зәӘ70е№ҙд»ЈпјҢи…ҢиҸңжҳҜеҶң家зҡ„еҪ“家иҸңпјҢиҠҘиҸңгҖҒиҗқеҚңиҸңеҗ„жңүе‘ійҒ“гҖӮжҜҸе‘ЁдёҖдёҠеӯҰпјҢжҲ‘们用зҪҗеӨҙ瓶е°ҸеҝғзҝјзҝјиЈ…ж»ЎдёҖ瓶и…ҢиҸңеёҰеҲ°еӯҰж ЎпјҢе°ұзқҖвҖңзҪҗеӨҙиҸңвҖқеҗғйҘӯж—¶пјҢжҲ‘们зңӢзқҖи…ҢиҸңзҡ„йўңиүІз”ұй»„еҸҳй»‘пјҢз”ұй»‘еҸҳйңүпјҢ瓶еӯҗйҮҢжңүж—¶й•ҝеҮәдәҶзҷҪзҷҪзҡ„з»’жҜӣгҖӮ
зӯүеҲ°жҳҹжңҹдёүпјҢеҗғе®ҢдёҖ瓶黑зҷҪзӣёй—ҙзҡ„и…ҢиҸңпјҢжҲ‘们еҸҲеёҰзқҖзҪҗеӨҙ瓶йЈҺйЈҺзҒ«зҒ«иө¶еӣһ家гҖӮжҜҸеҪ“иҝҷж—¶пјҢз©әз©әеҰӮд№ҹзҡ„зҪҗеӨҙ瓶еҗҢжҲ‘дёҖж ·еҪ’еҝғдјјз®ӯгҖӮеҸҲжҳҜж»Ўж»ЎзҪҗеӨҙ瓶и…ҢиҸңпјҢеҸҲжҳҜи…ҢиҸңйҮҢзҷҪзҷҪзҡ„з»’жҜӣпјҢеҸҲжҳҜйӮЈж®өиңҝиң’зҡ„еӣһ家и·ҜпјҢиҝҷж ·зҡ„еҫӘзҺҜд№Ӣж—…иҷҪ然иү°иӢҰпјҢдҪҶжңүеҝғзҲұзҡ„зҪҗеӨҙ瓶йҷӘдјҙпјҢеҝғйҮҢд№ҹж— жҜ”ж„үжӮҰгҖӮ
дёҖж¬ЎпјҢжӯЈеҖјиҝһз»өзҡ„йӣЁеӯЈпјҢеҪ“жҲ‘жҢ‘зқҖеҮ еҚҒж–ӨзЁ»и°·пјҢжіҘдёҖи„ҡж°ҙдёҖи„ҡд»ҺеҪ“ж—¶зҡ„еӨ§йҳҹйғЁжҠҠзұізўҫеӣһ家时пјҢзңӢеҲ°жЎҢдёҠзҡ„зҪҗеӨҙ瓶иҝҳжҳҜз©әзҡ„гҖӮеҺҹжқҘпјҢ家йҮҢзҡ„и…ҢиҸңеҗғе®ҢдәҶпјҢж–°еҒҡзҡ„и…ҢиҸңиҝҳиҰҒзӯүдёҠдёҖдәӣж—¶еҖҷгҖӮвҖңжҲ‘иҰҒдёҠеӯҰдәҶгҖӮвҖқж‘ҶеңЁжЎҢдёҠзҡ„зҪҗеӨҙ瓶еҘҪеғҸеҜ№жҲ‘иҜҙгҖӮжІЎеҠһжі•пјҢжҜҚдәІеҲ°йӮ»еұ…家еҖҹдәҶдёҖзў—и…ҢиҸңпјҢдёҖеҚҠиЈ…иҝӣдәҶзҪҗеӨҙ瓶гҖӮ
жҲ‘еёҰзқҖжҜҚдәІеҖҹжқҘзҡ„зҪҗеӨҙиҸңпјҢд»ҺйҷҲйҫҷж№ҫеҮәеҸ‘пјҢиҝҮз”°еҹӮгҖҒз©ҝжқ‘ж№ҫпјҢиө°иҝҮ黄家еӨ§ж№ҫжқҘеҲ°еӯ”家й“әпјҢеҶҚиө°дёҠеҮ йҮҢи·Ҝе°ұеҲ°дәҶеӯҰж ЎгҖӮдёҖи·ҜдёҠпјҢз”°йҮҺзҡ„зЁ»и°·з»ҝдәҶгҖҒй»„дәҶпјҢеҸҲз»ҝдәҶеҸҲй»„дәҶпјҢи·ҜдёҠзҡ„е°ҳеңҹйЈһжү¬пјҢжҠҠжҲ‘зҡ„иЈӨи…ҝвҖңжҹ“вҖқжҲҗдәҶзҒ°иүІгҖӮзҪҗеӨҙ瓶йҮҢзҡ„и…ҢиҸңйҰҷе‘ід»ӨжҲ‘еһӮж¶Һж¬Іж»ҙпјҢиҫ№иө°иҫ№й—»пјҢдјёжүӢжҠ“дёҖжҠҠеЎһиҝӣеҳҙйҮҢпјҢеҡјзқҖеҡјзқҖпјҢеҸӘжңүе°‘и®ёзӣҗе‘ізҡ„и…ҢиҸңйЎҝи§үжҳҜйӮЈж ·зҡ„йҰҷпјҢйӮЈж ·зҡ„з”ңпјҢйӮЈж ·зҡ„зҫҺгҖӮ
зҪҗеӨҙ瓶дёҺжҲ‘们еңЁж ЎеӣӯжңқеӨ•зӣёеӨ„пјҢз®ҖйҷӢзҡ„еҜқе®ӨйҮҢпјҢжңүвҖңйҘҝвҖқзқҖиӮҡзҡ®зҡ„зҪҗеӨҙ瓶пјҢжңүеҮ зүҮи…ҢиҸңиҙҙеңЁз“¶еЈҒзҡ„зҪҗеӨҙ瓶пјҢжҲ–иәәеңЁеҶ·еҶ°зҡ„з«№еәҠдёҖи§’пјҢжҲ–з”ЁдёҖдёӘеёғзҪ‘е…ңжҢӮеңЁеўҷдёҠпјҢжҲ–йқҷйқҷиәІеңЁеәҠеә•дёӢгҖӮдҪҸеңЁй•ҝжұҹиҫ№зҡ„дёҖдәӣеҗҢеӯҰпјҢеҒ¶е°”жңүеҮ еҸӘжІіиҷҫе’Ңи…ҢиҸңдёҖиө·иЈ…еңЁзҪҗеӨҙ瓶йҮҢпјҢжҜҸеҲ°еҗғйҘӯж—¶пјҢеҜӮйқҷзҡ„еҜқе®ӨдёҖдёӢеӯҗзғӯй—№иө·жқҘпјҢиҷҪ然еҸӘеҗғеҲ°дёҖеҸӘе°Ҹе°Ҹзҡ„иҷҫпјҢеҚҙж јеӨ–й«ҳе…ҙпјҢиҝҷд№ҹз®—жҳҜеҘўдҫҲдәҶгҖӮ
жңүж—¶зҪҗеӨҙ瓶йҮҢзҡ„и…ҢиҸңжҺҘдёҚдёҠжқҘпјҢж— еҘҲеҸӘеҘҪеҲ°ж®өеә—иЎ—дёҠд№°еқ—иұҶи…җжҲ–еҮ еҲҶй’ұзҡ„иҫЈиҗқеҚңпјҢеҗғеҫ—жҙҘжҙҘжңүе‘ігҖӮзҪҗеӨҙ瓶зӣ–жҳҜй“Ғзҡ®еҒҡзҡ„пјҢз”ұдәҺж°§еҢ–з»Ҹеёёз”ҹй”ҲпјҢжңүж—¶еңЁзҪҗеӨҙ瓶еҸЈз•ҷдёӢдәҶдёҖйҒ“йҒ“й”Ҳиҝ№гҖӮе°Ҫз®ЎеҰӮжӯӨпјҢжҲ‘们еҜ№зҪҗеӨҙ瓶иҝҳжҳҜзҲұдёҚйҮҠжүӢпјҢз”ЁеәҹзәёжҲ–еёғжқЎж“ҰдәҶж“Ұй”Ҳиҝ№пјҢжҙ—дәҶжҙ—瓶еӯҗпјҢеҸҲиҪ»иҪ»ж”ҫиҝӣд№ҰеҢ…гҖӮ
800еӨҡеӨ©зҡ„й«ҳдёӯж Ўеӣӯз”ҹжҙ»пјҢжҲ‘们еҡјзқҖи…ҢиҸңпјҢеҗ¬зқҖиҖҒеёҲжң—иҜ»гҖҠзҘқзҰҸгҖӢгҖҠжө·зҮ•гҖӢпјҢеҗ¬зқҖиҖҒеёҲи®ІжҺҲвҖңx+yвҖқ,зңӢзқҖиҖҒеёҲжқҝд№Ұзҡ„ж°ҙеҲҶеӯҗејҸвҖҰвҖҰзҪҗеӨҙ瓶йҮҢж—ўжңүдәәз”ҹзҡ„е‘ійҒ“пјҢд№ҹжңүзҹҘиҜҶзҡ„иҗҘе…»пјҢжӯЈжҳҜиҝҷдёӘдёҚиө·зңјзҡ„зҪҗеӨҙ瓶пјҢиҜ йҮҠдәҶе№іеҮЎеҰӮдҪ жҲ‘пјҢд№ҹжӣҫжңүиҝҮеұһдәҺиҮӘе·ұзҡ„й»„йҮ‘ж—¶д»ЈгҖӮе№іеҮЎзҡ„ж—ҘеӯҗпјҢз…§ж ·еҸҜиҝҮжҲҗиҜ—зҡ„ж·ұеҲ»йҒ“зҗҶгҖӮ
жқҘжәҗпјҡй„Ӯе·һж—ҘжҠҘ
дҪңиҖ…пјҡйҷҲеәҶи·ғ зҶҠзҫҺе…°